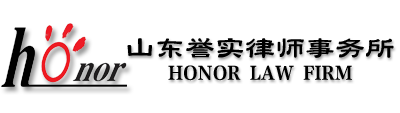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这场全民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必须依法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阻断病毒感染源头。由此,各地公安机关纷纷对一些拒不履行疫情义务的行为,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予以立案追诉。应当说,这是阻断病毒感染、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不得已而又切实有效的措施。确实,在这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有力的法治保障,传染病防治法等防控传染病法律法规需要得到良好实施,民众的良好法治观念、法律意识、守法习惯也需要在刑罚的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中得到提升。刑法作为担负“惩罚犯罪,保护人民”重任的最重要部门法之一,在重大突发事件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同时,司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部分。法院如何在这个特殊时期做好本类案件的审理工作,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案件审理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充分发挥刑事司法在重大突发事件的国家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乃是重中之重。
其实,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拒不履行疫情义务导致传染风险甚至带来严重后果的行为进行依法惩处,在刑法中早就有明确规定。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和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投放……传染病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早在2003年的非典(SARS)突发事件时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对此联合作出了《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为依法及时、从严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更是于2020年2月10日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新型冠状病毒作为具有很强传染性的病毒,行为人明知如此还拒不履行疫情义务,故意携带病毒频繁出入公众场所或参与集会等,从而将病毒以“传销”模式传播和扩散出去,严重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自然需要动用刑法以惩处。这既是阻隔病毒继续扩散传播的需要,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体现和要求。
然而,在拒不履行疫情义务案件的处理中,也需充分认识到本“重大突发事件”的特殊性,不可一刀切地简单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涉案者予以定罪处罚。毕竟,新型冠状病毒作为具有恐慌性的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民众和社会带来的心理压力是巨大的,并且还有其他复杂社会因素的介入,使实践中拒不履行疫情义务并带来传染风险甚至严重后果的行为,有其特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由此,对拒不履行疫情义务导致传染风险甚至严重后果的行为,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性处罚,需要综合案件的主客观情况具体分析。
综观当前实践中那些拒不履行疫情义务的行为,我们认为,需重点关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重视对拒不履行义务行为危害“公共安全”的考察。危害公共安全是危害不特定或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但就拒不履行疫情义务行为而言,除了考察其不特定性外,还应就场所轨迹、行为方式和接触人数等,考察其危险传播的“公共扩散性”。其中,在场所轨迹方面,对于那些在公共性场所如医院、超市等活动的,一般可认定为危害了公共安全,如《意见》指出,只有“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才可能构成本罪,便是从行踪轨迹上对本罪做出限制。而对于那些在较强“封闭性”场所如在家中、人流较少楼道等活动,因通常不会带来大面积传染,一般不宜认定为危害了公共安全。在行为方式方面,对于那些行为具有公共危害性的,如频繁参与赌博、酒宴,或向电梯吐口水等,应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而对于疑似病人违反隔离规定,偶尔进入公众场所,停留时间短且并未与他人交流的,由于造成病毒传播的可能性较小,也可酌情不认定为本罪。在接触人数方面,除需考察实际接触数量外,还应考察行为时一般可接触的人数,不宜仅依最终感染人数认定行为危害公共安全,如因特殊体质导致感染人数多,但行为本身一般无公共性危害的,不宜认定。
二是对本罪的主观故意不能简单地以危害结果论。本罪作为故意犯罪,在主观上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情况。如此两种不同的主观故意,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定罪模式。对于直接故意来说,因刑法总则规定了犯罪未遂等未完成形态,其定罪不是按行为结果而是按故意内容,包括是什么样的故意内容就依法定什么样的罪名,以及符合了刑法分则规定就是犯罪既遂,否则就是犯罪未遂等,并且若“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就按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若没有,就按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间接故意来说,就只能按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结果来定罪,也就是只有放任了“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才能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同时,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认定中,还需重视对行为“明知”的考察,不能简单地以严重后果直接推定行为的危险性。在本罪的“危险”认定上,是侧重于行为本身的危险性,而非后果的严重性。毕竟行为者在未认识到自身所带病毒的情况下,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并非是其主观恶性所支配下施行的。
三是本罪主观故意的认定具有特殊性。从实践中的本类行为来看,多数行为人对病毒传播是放任态度,属间接故意。但有人是在采取相关行为后才被确诊,主观认定存在疑惑。我们认为,实施行为后才被确诊,并不一定排除间接故意甚至直接故意的可能。本次《意见》将疑似病人纳入本罪处罚范围,也印证了这一观点。由于本次疫情具有高度传染性,一般具有明显发病特征,可结合行为人是否有就诊记录及明显症状、是否来源于疫区、是否做出防护措施及客观行为活动等综合判断。对来源于重点疫区,出现明显症状但拒不就诊或拒绝隔离,并频繁参与公众活动的,仍可成立故意。但这个故意认定需谨慎,不能将行为人违反管理规定的故意,直接视为具有本罪的故意。如对未产生明显症状且尚未确诊的,或家人患病但自身未被确诊的,为躲避隔离而乘坐交通工具,尤其是采取了防护措施(如戴口罩)的情况,不宜一律认定为故意。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严重后果的,成立过失类犯罪或不构成犯罪。
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认定中,需要特别注意本罪与相关犯罪的界分问题。其中,最为复杂的是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界分。据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第四款的规定,“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有传播严重危险的,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为维护公共安全,国家卫健委于2020年1月20日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对于“拒绝执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应以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予以立案追诉。这意味着,在当前的规范性文件下,对拒不履行疫情义务导致传染风险甚至严重后果的行为,也有可能成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据此,实践中需重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行为是否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其中,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成立,只要实施了违反了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传染病防治管理制度及其卫生检疫管理措施系列行为,而不要求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二是主观上是否是过失。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主观上为过失,即行为人虽然故意违反防疫规定,但对造成“传染病传播或传播的严重危险”结果持过失形态,这一结果的发生是违背行为人意志的。如果行为人明知自身行为会带来冠状病毒传播或严重传播风险,并刻意追求或放任发生,则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此,实践中为逃避隔离,违反上报规定,仅瞒报、隐瞒行程但并未频繁出入公众场所的,或亲密接触者基于侥幸心理,不严格采取防护措施,不严格遵守隔离规定,或患者家属拒不提供行踪信息,以致大大加重疫情管理难度,进而加剧疫情传播风险的,构成的应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另外,本罪还涉及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寻衅滋事罪和妨害公务罪的界分。对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分,基本上只要考察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就可以做到。对于病毒携带或疑似携带者在公众场所向他人吐口水等行为,不是故意传播病毒或没有过失带来实害病毒传播后果,但造成医疗或公共秩序混乱的,可以考虑构成寻衅滋事罪。对于采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检疫、隔离管理行为,在属于非情节显著轻微的情形下,可以考虑成立妨碍公务罪。由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较重,竞合时需以重罪处理,在未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程度时,应妥善运用他罪,以免不当扩张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
最后,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疫情治理是综合治理,需要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进行现代化处置,不可片面夸大刑事手段在其中的作用。具体需要将个案置于由传染病防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等组成的相关法律体系中,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审慎选取民事、行政、刑事等手段,进行多元化治理,以避免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疫情治理效果。其中,对于那些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反响不强烈的行为,能够以民事和行政手段处理的,就尽可能不要以刑事手段处理,而应秉承“坚持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可判可不判的不判”的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在有效实现疫情治理的同时,让人民群众从每个刑事裁判感受到公平正义,以贯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作者:石经海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主任;金舟为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