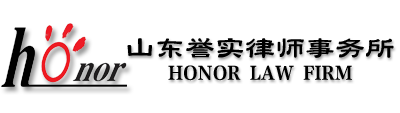目前,人民法院案例库中尚未收录快递员窃取快递内财物的权威案例,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此类行为的定性存在分歧,有的认定为盗窃罪,有的则定性为职务侵占罪,导致“同案异判”现象,直接损害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司法公信力。对于快递从业者与社会公众而言,由于缺乏明确、权威的行为指引,难以形成稳定的法律预期。同时,这也使得法学研究与教学缺乏鲜活的实践样本,不利于相关法律适用共识的形成与统一裁判规则的提炼,亟待通过权威案例予以明确和指导。
一、已生效裁判的类型化典型案例
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涉及快递员窃取快递内财物行为的裁判文书进行系统梳理,尤其注重对经二审终审的典型裁判展开重点检索、分类整理,可发现该类型案件在各地均有出现,但裁判结果有盗窃罪和职务侵占罪两种定性。
(一)认定为盗窃罪的案例
1.赵某盗窃案
某快递从业人员赵某借助职务之便,将价值7万余元、不属于其配送范围的万国牌IW356504型手表非法占为己有,事后以2.2万元的价格出售。一审法院判定赵某构成职务侵占罪。二审法院认为赵某利用工作便利实施的盗窃行为,改判赵某犯盗窃罪。
2.廖某盗窃案
廖某在分拣快递过程中,发现一个已扫码入库、疑似装有贵重物品的快递包裹,遂趁周围同事不备将该包裹转移至自己负责的区域,待其拆开包裹后将其中的15件黄金首饰非法占为己有。法院认为廖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盗窃罪。
3.熊某、李某盗窃案
某快递从业人员熊某与李某装卸作业时,熊某向李某提议盗窃快递包裹内的香烟。二人共同盗得香烟六条,总价值达人民币5400元。经法院审理认定,被告人熊某、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通过秘密方式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
(二)认定构成职务侵占罪的案例
1.杨某职务侵占罪
某速运公司从业人员杨某采用大件掩藏小件躲避扫描的方式,盗走一部价值1999元的小米手机。一审法院认为,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构成盗窃罪。二审法院认为,杨某作为某速运公司工作人员,利用经手本单位财物的职务之便侵占财物,属职务侵占性质,但因财物价值未达1万元定罪起点,不应以犯罪论处。再审法院维持了二审判决,并指出区分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的关键在于是否利用职务之便。
2.黄某职务侵占罪案
某快递人员黄某割开一快递箱发现其中有4袋黄金饰品,遂窃取3袋饰品藏匿后将箱子送至金店。一审法院认为,黄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的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盗窃罪。二审法院认为黄某身为公司的工作人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公司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
3.俞某职务侵占案
快递员俞某误领取不属于其投递区域的快件后,将快件里的6部小米手机据为己有。法院认为,被告人俞某身为速运有限公司员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
二、典型案例裁判分歧的焦点
1.“经手”行为的性质
快递员“分拣”快件是其工作的必要一环,“分拣”行为性质的判断是法院裁判意见分歧的焦点之一。如在廖某盗窃案中,法院判定快递员的分拣行为属于单纯的体力劳动,快递员并未利用其职务上独立主管、管理、经手财物的权力。因此,分拣环节的“经手”行为仅为工作必要行为,并不属于职务行为范畴。然而,在杨某职务侵占案中,法院持有不同观点,认定分拣环节的“经手”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的一部分。这种对同一行为性质的不同认定,直接致使相同行为在不同案件中被赋予不同的法律定性,进而对案件判决结果产生影响。
2.“实际控制”的标准
从上述案例中可见法院对“实际控制”的裁判标准存在明显差异。如在俞某职务侵占案中,法院认为因快递处于俞某独立支配的快递车上,此情形已构成实际控制。而在廖某盗窃案中,法院则判定,分拣环节中的短暂接触不足以构成实际控制,此时快件仍然处于快递公司集中的物理控制与监管之下,其管理权并未转移至快递员个人。这种对“实际控制”标准的不同把握,使得相同或类似行为在不同案件中获得不同的法律评价。
3.“职务便利”与“工作便利”的界限
在此类型化案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分拣行为在不同案件中得到了截然相反的认定。如在杨某职务侵占案中,法院认为“经手并临时性实际占有快递件”的行为是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而在廖某盗窃案中,法院则判定类似行为仅为利用工作便利,而非职务便利。这种界限的模糊性,使得司法实践中对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区分变得复杂且困难。
三、职务侵占行为手段及“利用职务便利”的研判
职务侵占罪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典型财产犯罪之一,其核心特征在于“利用职务便利”实施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的行为。以下从常见行为手段及“利用职务便利”的司法判断标准两方面展开分析:
从职务侵占行为的常见手段看,实践中,行为人通常借助自身职务形成的主管、管理、经手单位财物的便利条件,采用多种隐蔽方式转移、占有单位财物,主要包括以下类型:一是直接侵吞型,表现为将自己合法持有的单位财物(如现金、货物、应收账款等)直接据为己有,且未按规定入账或上报。例如,出纳人员收取公司营业收入后,未存入公司账户而是私自挪用;仓库管理员将库存货物盗卖后谎称丢失。二是虚报冒领型,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通过虚假报销、冒领等方式骗取单位财物。例如,编造不存在的业务招待费、差旅费等支出,伪造签字或凭证向财务部门套取资金;冒用他人名义领取工资补贴。三是关联交易型,表现为利用对单位购销、采购、合作的决策权或操作权,与关联方(如亲属控制的公司、合作方)串通,以不合理高价采购或低价销售,使利益输送至关联方后再转归个人所有。例如,负责人甲指示单位从其妻子经营的供应商处高价采购原材料,差价部分由妻子公司返还给甲个人。还有截留应收款型、平账掩盖型、借用第三方工具型等。
从“利用职务便利”的司法判断标准看,“利用职务便利”是职务侵占罪区别于普通盗窃、诈骗罪的关键要件,需结合主体身份、职责内容、行为方式综合认定,具体可从以下的维度去把握:前提条件是必须具备“职务关联性”,行为人必须因担任一定职务而合法持有单位财物的管理权、经手权或支配权,而非单纯利用工作环境熟悉、易于接近目标等便利条件(后者可能构成普通财产犯罪)。职务不限于正式员工的岗位职责,也包括临时聘用、授权委托等情形下的实际职权(如项目经理虽无编制,但对项目资金有审批权)。核心要素是掌握“职务便利”的具体内涵,即“职务便利”本质是职务赋予的对单位财物的管理、控制或处置权限。
若仅利用工作中形成的“机会便利”(如知晓保险柜位置、掌握领导作息时间),而非基于职务本身的管理、经手权限,则不认定为“利用职务便利”。例如,清洁工趁无人之机窃取办公室财物——属盗窃而非职务侵占;在认定职务侵占罪时要综合考量主客观一致性,司法机关需审查:客观行为是否依托职务范围内的操作流程(如使用公章、财务系统账号、提货单等);主观明知,行为人是否认识到自己的职务权限是实现侵占的必要条件;因果关系,财物被侵占的结果与职务权限的行使是否存在直接关联。
综上,职务侵占罪的本质是“监守自盗”,其手段围绕“利用职务便利”展开,涵盖侵吞、骗取、关联交易等多种形态。司法实践中,“利用职务便利”的核心在于行为人对单位财物具有职务上的管理、经手或处置权限,且该权限是实现侵占的必要条件。准确界定这一要件,需结合行为人的职责范围、行为方式及财物控制的因果链条进行综合判断。
四、快递员窃取快递行为的核心标准与规则构建
(一)核心标准:“实际控制”理论
应将快递员是否对快递形成“独立的、排他性的实际控制”作为判定其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的核心准则。在司法实践中,判定是否形成“实际控制”应当综合考量以下因素:其一为物理控制精准度:财物是否处于行为人的独立支配空间(如个人配送车辆、专用货架等);其二为保管责任归属:依据单位规章制度或行业惯例,行为人是否对财物承担保管、看管职责;其三为单位控制力的弱化程度:单位的监控举措、管理制度等对财物的控制力是否因行为人的职务行为而实质减弱;其四为处置权限范畴:行为人是否被授权对财物进行必要的处置(如临时保管、异常情况处理等)。
(二)规则构建
1.基于业务环节划分的裁判规则
其一,在分拣环节窃取快递的情形,应以是否对快递实现实际掌控作为定性标准。在分拣环节,若快递员通过对快递实施实际控制而确立起独立的保管关系,其侵吞行为应认定为职务侵占罪;若仅为短暂接触、经手,未形成实际控制,则应认定为盗窃罪。具体的判断要素包括:快递是否分拣至个人负责区域、快递员对快递的控制能力、是否具备独立处置权。
其二,在运输环节窃取快递的,应认定为盗窃罪。对于有封志的运输,运输人员仅对运输车辆的外包装享有占有权,内容物仍由快递企业占有。运输人员窃取内容物的,构成盗窃罪。
其三,在派送环节窃取快递的,需区分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在派送环节,快递员依据职务要求独立负责特定区域的派送工作,对快递包裹拥有实际控制权。根据刑法规定,快递员侵吞本人正常派送范围内的快递,若利用职务便利将其非法占为己有,构成职务侵占罪;若侵吞通过错误分拣等方式获得的非本人派送范围的快递,则构成盗窃罪。
2.基于具体情形划分的裁判规则
其一,区分职权范围。快递员窃取职权范围内的快递,即自己配送区域的快递,利用职务便利经手、管理财物,构成职务侵占罪;窃取职权范围外的快递,即非自己配送区域的快递,仅利用工作便利接近财物,构成盗窃罪。
其二,区分行为公开性。在司法实践中,快递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秘密窃取他人财物,例如采用重新封装、隐蔽携带等手段,通常会被法院认定为盗窃罪。秘密性是盗窃罪的重要特征,与职务侵占罪通常具有的公开性、利用职务性形成鲜明对比。
其三,区分保管责任。若快递员对快递负有保管责任,如派送环节的快递员需对派送范围内的快递承担保管义务,则其侵吞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若仅为短暂接触或经手,如分拣环节的一般分拣员,则对快递不负有保管责任,其窃取行为构成盗窃罪。
(作者王沛系河北经贸大学教授、法学博士;赵巍键系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人民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