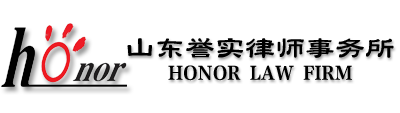在电子支付高度普及的当下,错误汇款行为显著增多。误将款项汇入被人民法院冻结的被执行人账户,属于错误汇款的一种特殊情况,汇款人往往会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针对误汇款项的权属认定、能否排除执行等争议焦点,裁判思路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分歧,有待统一裁判尺度,以平衡误汇款人的合法权益与其他利益之间的冲突。
一、误汇款项至被冻结账户类案件的审理现状
误汇款项至被冻结账户类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对其声称误汇入冻结账户的款项,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也即误汇款人对案涉款项享有物上请求权,还是仅有不当得利请求权。就此,当前多数判决采用双重审查:先审查是否确系误汇,以排除恶意串通;再审查款项是否特定化,以决定适用“占有即所有原则”导致不当得利,抑或因法律行为被撤销导致原物返还(不能或没必要返还的,则折价补偿)。不过,模式趋同未能带来观点的一致化。围绕汇款行为确系误汇的法律后果、账户权利人是否对账内款项构成占有等问题,不同审理层级的法院之间、各地法院之间,尚存诸多观点冲突。
笔者分析发现,争议焦点汇集于“占有即所有”原则。一旦确认误汇事实,案涉款项的权属即成为焦点。货币作为种类物,受“占有即所有”约束。误汇款人主张原物返还,须证明案涉货币已特定化,脱离了种类物属性。因此,货币是否发生特定化进而逸出“占有即所有”的适用范围,成为法庭审查的重心。“占有即所有”源于德国学者马克斯·卡塞尔于1937年发表在《民法实务档案》的论文《物权法上的货币》,后经研究发展,扩张为货币权属认定的普遍原则。其核心内涵为:货币的占有与所有合二为一,占有人被推定为所有权人。此推定具有无因性,不受占有原因、占有人主观状态等因素影响。货币所有权的取得与消灭仅依占有变动而定,原权利人丧失货币占有即丧失其所有权,仅能主张债权请求权。
围绕“占有即所有”的适用边界,司法实践中呈现出三类截然不同的裁判立场。部分判决将“占有即所有”极致扩张,认为货币为种类物,一经交付即发生所有权移转。有些判决则将其极致限缩,认为缺乏真实合意的支付并不导致货币权属转移。多数判决则持折中立场,认为货币一经收款人占有即归其所有,除非货币已经作特定化处理,但货币特定化的审查标准扮演着一个高度灵活的调节阀角色,即便同属折中立场,不同的审查标准也会带来不同的裁判思路与结果。
二、“占有即所有”的法理思考与规则重构
通常认为,“占有即所有”原则旨在解决两类结构性的利益冲突:其一,原权利人与非法占有人之间。例如,误汇款人主张撤销误汇后,本可享有原物返还请求权,但标的货币与其他货币已混合而难以区分。因为无法返还原物,民法遂赋予其不当得利请求权予以补救。其二,原权利人与善意第三人之间。货币误汇至某账户后,收款人通过正常交易支付给不知情的第三人。经利益衡量,交易安全与货币流通秩序更为优先,误汇款人的原物返还利益退居次位。第二类利益冲突争议不大,第一类则尚存争议。笔者认为,从“占有”到“所有”的逻辑,并非“即”字所能简单概括。
审判实践中,极少数判决对“占有即所有”作绝对解释,几乎仅凭“占有”推定“所有”,该立场有失偏颇。占有本身并不必然导致货币所有权转移,关键的法律事实在于“混合”。混合指不同所有人的动产混杂,致难以识别或识别费用过高。占有与混合是两个独立时点。占有是前提,混合才是直接触发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例如,乙收到甲误付的百元纸币后,将其单独夹于书中,占有而未混合,则该纸币所有权清晰,甲享有原物返还请求权。此时若适用“占有即所有”认定甲仅享有债权,明显缺乏适用基础。
审判实践中,大多数判决依据案涉资金是否特定化确定物权归属。该思路具有合理性,但需要校准。“特定物—种类物”判断,不能完全置换“混合及不能识别”判断。换言之,种类物置于同一占有之下可能不混合,特定物则可能发生混合。前者例如前举百元纸币夹于书中的情形。后者例如,一件小型二手玩具被送入回收站,归入堆积如山的废旧玩具之中。该玩具虽为特定物,但因无法识别而发生混合。因此,认为案涉资金特定化就可以返还、未特定化就不应返还的观点,其逻辑似是而非。
有判决依据案涉资金是否发生混合确定物权归属。该思路更为合理,但仍有值得进一步完善之处:未能充分考量货币作为种类物的高度同质性和交易上的可替代性。一个挑战传统的观点是,同种种类物在法律上一般不构成混合。从概念本质看,决定动产是否构成混合的,不是物理属性,而是法律属性,即交易与确权的现实需求。同种等额货币混杂后,物理上确实难以分离和复原。不过,因其价值与功能等价,凭金额即可低成本、即时区分,无需识别每张纸币的物理特征。纸币的冠字号码、流水号码、新旧程度等物理性状确系独一无二。但这些差异仅在收藏、防伪、溯源、追赃等语境下有意义,在民商事语境下无法律意义,属于无关因素。
“占有即所有”论者常举出如下例证:一张百元纸币被甲误支付给乙,与乙的其他纸币混合后,甲丧失物权,仅能主张不当得利返还之债权。然而,此推论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符:其一,货币是特殊种类物,交易上具有可替代性。混杂纸币虽物理上不可分,但法律上因等值可替代而无需区分。其二,误付人的真意在于追回其货币价值,而非索回特定的纸张(某张纸币)。其三,赋予物权请求权效率更高,可避免降格为债权制造的清偿劣势与额外成本。由此可见,在法律上无必要、当事人无意愿、经济上不效率的前提下,固执于物理形态,据此剥夺权利人的物权,有制度冗余之嫌。
综上所述,在货币错付场合,既不应直接推定“占有即所有”,也无须审查案涉货币是否特定化或已发生混合。除非货币已流转至善意第三人,否则误付人应当享有物权返还请求权,其主张返还的客体是“法律上的原物”而非“物理上的原物”。司法实践应尊重交易习惯与当事人可推知的真意。以上思路适用于所有种类物,尤其是价值符号属性强而空间实体属性弱的货币、有价证券等特殊种类物。
三、误汇款项至冻结账户的权属审查思路
在执行异议之诉中,认定权利人(误汇款人)能否排除强制执行,可依下述三阶段审查:第一阶段,审查是否确系误汇行为。若否,则直接驳回异议请求;若是,则进入下一阶段。第二阶段,审查案涉款项是否发生混合。已混合的,异议人仅享有不当得利返还债权,需平等受偿;未混合的,进入下一阶段。第三阶段,审查款项是否由善意第三人合法取得。已合法取得的,异议人仅享有不当得利返还债权;未取得的,认定其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物权权益。
1.错误汇款事实的司法查验。第一阶段审查最为关键。确认误汇事实不仅是后续审查的总前提,也能够排查一个核心风险,即汇款人与收款人是否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查验角度包括但不限于:(1)汇款人发现错误后,是否及时通过交涉、起诉或报警等主张权利;(2)操作中是否存在误汇诱因,如收款账号、户名相似,或选择列表中正确与错误账号相邻;(3)转账时间、金额能否与合同、发票、付款凭证或转账附言等内容印证;(4)汇款人与收款人之间,历史上有无业务往来或关联关系;(5)汇款时间先于还是后于账户冻结,前者无法排除串通嫌疑,后者则显著降低了串通的可能性。
2.货币混合状态的法律认定。第二阶段审查案涉货币的法律状态。当前判决多聚焦于货币是否特定化而脱离种类物属性,甚至有判决持绝对化立场,认为货币一经交付所有权即转移。如前文所述,此类审查失之精准,应予简化调整。货币作为特殊种类物,其相互的物理融合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混合,因此“是否混合”无需审查。加之特定物亦可能混合,因此“是否特定化”的审查亦无必要。
目前立即转变裁判路径恐不现实,但最近诸多判决已形成一种折中路径,借助法律拟制技术降低审查标准,实现了间接校正。这些判决又可分为两种思路,部分判决降低了“货币特定化”的认定标准,例如认定案涉款项因账户冻结,未与收款人其他货币混合,据此推定为特定化款项。另有判决则降低了“货币混合”的认定标准,例如认定账户冻结后没有其他款项进入,视为案涉款项未发生混合。
3.善意第三人取得因素考量。第三阶段审查案涉货币是否已由善意第三人合法取得。若是,异议人即丧失其对原款项的物上请求权,其法理依据为,在此情况下,交易安全与货币流通秩序利益优先于异议人的个别物权利益。事实上,因账户冻结已有效阻止货币再流通,故在实践中,除特例情形外,第三阶段审查鲜有发生,其实际重要性相对较低。
回顾此类案件,既有判决的贡献在于确立了清晰的递进审查模式:先审查误汇事实,再审查货币特定化。其中,针对误汇建构的审查细则体系颇具价值。优化空间主要在于反思当前对货币“特定化”及“是否混合”的严格审查,是否对误汇款人的物权权益限制过度。其次在于补充误汇款人与交易第三人之间的利益衡量。此外,强制执行的成本与效率因素也不妨纳入考量。
笔者认为,也许更为彻底的方式是完全省略对货币特定化的审查。事实上,货币的会计混合不构成难以识别,加之账户冻结已阻却货币流通,故只要确系误汇,即应支持排除执行。更为务实方案是,保留特定化审查但大幅放宽标准,已有裁判体现该思路。此外,也有判决认定,付款人与收款人均未占有货币,从根本上切断“占有即所有”的适用前提,亦具有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林凯;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王晓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