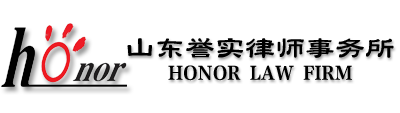【核心观点】
“羊老大”商标纠纷案中引发出我国商标制度中诸多重大的法律实务与理论问题,包括:商标权属纠纷与商标注册争议的不同调整范畴及判别规则;商标行政复审前置程序的适用条件;商标权属争议中的司法主管权的效力问题;商标转让法律制度的立法变迁问题;商标析产法律制度和商标权属确认与诉讼时效制度等尖端法律问题。作者通过对民法与商标法制度的深入研究后得出了与众多专家意见不同的前沿观点。
【争议与主张】
原陕西榆林地区羊老大制衣有限公司(下称“榆林羊老大”)于1997年5月21日获准在第25类商品(服装)中注册“羊老大”(艺术体文字)商标。2001年6月,“榆林羊老大”之主要股东又在北京设立关联企业北京羊老大服装有限公司(下称“北京羊老大”)。
两公司一度曾共同使用并先后对该商标有过两次互相转让行为:第一次在2001年6月11日,“榆林羊老大”许可“北京羊老大”使用上述文字商标,并承诺“已将该羊老大商标转让给了北京羊老大,待北京羊老大注册登记后,该商标即为北京羊老大所有”,但两公司并未实际办理该商标的转让核准程序,商标注册证原件一直由榆林公司持有;第二次在2002年4月20日,两公司签署《联合声明》,内容为“经双方友好协商,北京羊老大服装有限公司,愿将本公司注册商标“羊老大”品牌无偿转让给榆林市羊老大制衣有限责任公司”。此后,“榆林羊老大”单独申报并于2002年5月14日获准注册了“羊老大(图形)”和“羊老大(图形+文字)”商标。
奇异的是,在“榆林羊老大”获准注册上述两图形系列商标仅3日后即2002年5月17日,“北京羊老大”即向国家商标局递交了针对该系列商标的《转让注册商标申请书》,申请将其转让至自身名下。国家商标局予以核准,但并未通知“榆林羊老大”亦未收回其所持有的“羊老大”系列商标注册证书,这样就出现了同一系列商标由两个商标注册证持有人的现象。
“榆林羊老大”获悉转让消息后随即向国家商标局提出质疑:1,除《联合声明》外其与“北京羊老大”之间没有任何新的“转让协议”,商标局在不核对商标转让法律关系真实性的情形下何以能够办理商标转让过户手续?2,商标局仅仅依据受让方提交的“注册商标转让申请表”即办理商标过户手续是否存在其程序合法性瑕疵?3,在该申请表“转让方”一栏中加盖的“榆林羊老大”企业公章是已被废止的旧公章,原榆林地区经国务院批准于2000年7月起已“撤地改市”,榆林公司章之行政区域前缀已由原“榆林地区”改为“榆林市”,并且其所持的商标注册证原件中记载的权利人亦是“榆林市”羊老大公司而不是“榆林地区”羊老大公司,国家商标局何以能对如此明显的瑕疵申请予以核准?对于上述质疑,“榆林羊老大”被告知有关商标转让纠纷应向法院寻求解决。两公司遂起商标转让合同及权属纠纷。本案经陕西榆林中院和陕西高院两审终审,“羊老大”系列商标全部被判归榆林公司所有。“北京羊老大”申请再审,在双方就权益补偿及系列商标的归属达成调解协议后,该系列商标最终全部归“榆林羊老大”所有。
诉讼中,“北京羊老大”主张:1,“联合声明”属于“赠与”合同,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2,法院对本案没有直接管辖权,商标注册争议应当先由行政复审后,才能以行政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争议,陕西两级法院直接以民事诉讼审理本应属行政诉讼审查范畴的案件系错误的。
“榆林羊老大”主张:1,双方所签订的“联合声明”实际上是商标权属确认合同,该合同有效并应得到继续履行;2,在没有任何关于“羊老大”系列商标新的“转让协议”时,仅凭加盖已废止印章的“商标转让申请表”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转让法律关系;3,法院对本案享有民事纠纷主管权。
引人注目的是,两公司曾均召开过涉及自身利益关切的“专家论证会”,并借助媒体报道来“放大”自身诉辩主张话语权借此给受案法院施加影响。
代表“北京羊老大”利益关切的专家学术会议于2005年6月8日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会议室召开,会议主题是“地方法院对国家部委的管理权力的漠视、限制和剥夺??陕西省“羊老大”商标案判决中存在的法律问题”。与会专家有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人大法学院院长王利明,国家商标局商标法专家吕志华,中华商标协会中企商标发展中心副主任郭修申等;代表“榆林羊老大”利益关切的专家会议于2005年8月14日由中国企业家协会组织召开,与会专家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立新,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君等。
一时间,围绕“羊老大”系列商标案中的法律问题,两大阵营之专家观点歧见明显,舆论导向各执一端。那么,到底应当如何正确认识和解析本案中有关法律规则?请看下文“规则与解读”。
【规则与解读】
笔者认为,本案主要法律问题包括:1,双方纠纷性质是商标注册争议还是商标权属争议?该二者有何区别?2,法院对商标转让合同或权属纠纷有无直接的主管权?当事人是否可以既选择民事诉讼程序又选择行政诉讼程序来寻求救济?3,关联企业间对商标进行“无偿转让”是否应当适用合同法“赠与”制度进行调整?本案“联合声明”属何种性质的法律文件?4,商标行政主管机关在核准商标转让时是否应当要求相关当事人提供“转让协议”并进行形式要件的核实以防止“盗转”可能?5,商标权属争议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一、关于商标注册争议与商标权属争议的界别问题。
笔者认为,“羊老大”系列商标案是典型的商标权属纠纷案,对此类纠纷一旦审之不详则易与商标注册争议案相混淆而引发误判。因二者之间在争议属性、救济程序等方面存在质的不同。
商标注册争议“争”的是“在后注册”的商标应否有效存续的问题?在此类争议中,提出异议一方之根本目的是要“否决”被争议商标的存续效力;商标权属纠纷“争”的却是该商标应当归谁的问题?对该被争议的商标是否应当存续各方并无争议且均是力争维持的。可见,注册争议是对商标主管机关所作出的各类核准具体行政行为的有效性持有异议,故应适用商标复审及行政诉讼程序。但商标注册争议的本质仍是民商权利争议,因为此类商标行政诉讼实际是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是借助行政程序来判别商标注册人民事权利的有效性;而商标权属争议是平等民事主体对该商标权的归属发生纠纷,认为争议商标应归自己而不是他人,故与商标核准行政行为无关。当然应当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而与商标复审和行政诉讼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是二者之间的第一个不同。
商标注册争议一般因三种缘由引发:一是存有“在先权”的一方认为争议商标损害其在先权,所以要在该商标的注册进程中阻止其有效注册从而引发争议;二是虽不享有在先权但与在后已被核准注册的商标存在有利害关系的主体可以申请撤销注册商标,对该商标既存效力提出异议而引发的争议亦是注册争议;三是既不享有在先权,亦与在后注册的商标无利害关系的任何主体对违反商标法禁用条款的注册也可以提出异议。
商标权属争议则在争议各方之间存在一个必然的前置性基础法律关系,即争议方此前围绕争议商标曾有使用、注册、许可、转让、授权、共用、信托等不同形式的民商事交易法律关系。并因商标权利之归属、使用及对有关约定和履行发生争议后引发商标权属争议。这是二者之间的第二个不同。
二、关于商标权属争议中的司法主管权与裁判权效力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专家们有不同的看法。如中华商标协会中企商标发展中心副主任郭修申就认为(见2005年06月28日法制日报报道):商标法第41条明确规定商标争议的解决机构是商标评审委员会,第43条明确规定双方对评审委员会做出的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这是行政诉讼,而不是民事诉讼。陕西的两审法院直接通过民事诉讼来审查国家商标局作出的行政行为,显然超出了民事诉讼的管辖范围,违反了商标法设置的行政前置程序。如果所有的法院都用民事诉讼来直接审查行政行为,那么商标法还有何用?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平(见2005年06月28日法制日报报道)也认为:商标权的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必须经过申请、审查、核准公告等特定的行政程序。尽管TRIPS协定中规定了司法审查权,我国商标法的修改也体现了这一原则,但当行政程序没有启动或没有完成,司法程序不能进行确权,一定是行政程序在先,司法程序在后。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旭东则认为,这个案子根本的性质属于商标权转让的纠纷。因而也就属于一个民事权益争议的纠纷,因为商标权就是一种民事权利,商标权的转让而引发了一种纠纷,当然是民事纠纷。进入司法程序,也就是民事诉讼。赵旭东认为:法院直接受理商标权转让的纠纷,并没有超越了管辖权限,并不是说所有的商标争议,包括商标的注册争议,商标的转让争议都要商评委先裁定,再去法院。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立新也认为,凡是涉及到权属问题都应该是民事诉讼,法院应该按照民事诉讼程序一审二审来解决这样一个权属争议的问题。这个案件用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应该是有道理的,有根据的。
笔者认为,否决本案司法管辖有效性的观点显然是将商标的注册争议与商标权属争议两类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相混淆的产物。因为,我国的商标法是商标行政管理法,其全部制度设置中,只调整第一层级的权利如因注册、续展、转让核准、驰名化认定、与市场秩序有关的使用等引发的商标原始权利纠纷,对涉及第二层级的权利如权属、转让、合同纠纷等需要通过确认继受权利基础性民商法律关系的纠纷则并不归商标法调整。因此,所有关于商标继受权利的基础性法律关系纠纷均应由我国民法、合同法等法律体系调整,而与商标法中的注册争议制度并不相涉。
根据前述关于商标注册争议与权属纠纷的判别法律规则,“羊老大”系列商标案是典型的商标权属纠纷。首先,两个“羊老大”公司显然没有任何一方否认“羊老大”系列商标的存续效力,而注册争议中则在先权一方必然要否认争议商标的存续效力;其次,两个“羊老大”之间事先存在着关于争议商标的转让、共同使用等基础性法律关系,但注册争议中则各方不存在此类法律关系;第三、北京公司方面只是对“联合声明”中所约定的商标转让效力存有异议;而榆林公司方面则对北京公司没有“转让协议”作为支撑的“商标转让申请表”所代表的转让法律关系之真实性及有效性持有异议;第四、最高法院关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本身即设有“商标权属纠纷”和“商标转让合同纠纷”等独立案由。毫无疑问,本案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因内部权益处分行为效力及履行方面的纠纷,与是否应经商标评审委员会行政复审无关,当然也不可能涉及到行政诉讼程序机制的启动问题,也就不存在当事人享有对行政或民事救济程序选择权的问题。因此,将商标权属、转让纠纷误认为是商标注册争议并要求以行政复审和行政诉讼程序进行权利救济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三、关于商标司法裁判权与商标行政核准权的相互制约问题
国家工商总局商标法专家吕志华(见2005年06月28日法制日报报道)在评析本案时曾认为:根据商标法第39条规定,转让注册商标经商标局核准后予以公告。受让人自公告之日起享有商标专用权。商标权是须经法定程序才能予以确立的权利,转让商标是确立新的商标权利人的过程,也必须经过法定程序,即商标局的核准和公告。未经商标局核准并公告的商标转让行为,其受让的注册商标不具有法律效力。法院即使做出有效的关于商标权属的民事判决,也不意味着当事人就自动取得了商标专用权,商标专用权依然属于商标局注册档案簿中载明的商标权利人,也就是现在有效的《商标注册证》上标明的注册人。
应当说,上述观点如果用于解读商标注册争议机制则觉尚可,但其关于否认司法裁判权终极效力的结论则值得商榷。加之,“羊老大”系列商标纠纷一案根本与注册争议无关,所以其结论当然是基于错误判断基础的产物。笔者认为,实务中类似有本案中的“无偿”或有偿处分商标权情形的,受让方有权要求另一方承担对转让合同的继续履行义务,并根据此类判决向商标主管机关直接申请过户。因此,在一方持有商标注册证的情形下,司法机关完全有权用确权判决对商标权属进行重新确认,并不受商标注册证所记载权利状态的限制。此时,法院的司法确权判决效力必然高于商标注册证,其具有直接否决和剥夺注册人商标权的法律效力。而且,国家商标局对法院的司法确权裁判负有协助执行义务,不得以商标权属确认权“专属”于商标主管机关为由而拒绝协助执行。事实上,商标主管机关只有正常的商标行政核准权,对涉及商标民商事权益纠纷并不享有确认权。
四、关联企业间对商标权属的“无偿”处分是否应适用“赠与”及“撤销”制度?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知识产权专家金勇军对此认为(见2005年06月28日法制日报报道):“联合声明”可以视作合同,其内容是“无偿转让”,显然属于赠与合同。合同法第186条明确规定赠与人具有撤销赠与权。“北京羊老大”在一审中已经公开宣布撤销这种赠与行为,依照合同法,“联合声明”随即失去法律效力。如果赠与人不履行赠与行为或撤销了赠与行为,受赠人能不能依据赠与合同,要求赠与人履行赠与义务?合同法第188条明确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本案的赠与声明显然不属于上述内容,因此,“榆林羊老大”不能根据“联合声明”要求“北京羊老大”转让商标权,法院也不能判决“北京羊老大”履行无偿转让商标的赠与合同。
笔者认为,上述“无偿转让”并不属合同法中的“赠与合同”法律关系。赠与合同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当事人之间不可能存在民商事交易法律关系,而本案纠纷双方是主要股东混同的关联企业,是商事主体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双方所签署的“联合声明”实际是关联企业内部对商标权属进行“析产”的法律文件,也是关联企业内部股东所作出的决议性法律文件。在析产法律关系中,无偿转让方当然无权套用赠与合同法律制度来行使撤销权,否则等于单方面撤销了公司内部决议。
事实上,在公司商标实务中这种内部析产法律文件的现实表现形式繁杂。诸如,有商标转让合同、许可协议、联合声明、单方承诺、使用协议、分割协议、注册协议、委托注册书、商标信托管理协议等多种法律文件表达方式,应当注意判别其本质法律关系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如果将某一关联企业向另一关联方“无偿转让”商标权认定为“赠与”的话,则意味着任何关联企业均获得了利用赠与撤销制度而享有拒绝执行公司内部决议的权利,故机械套用赠与撤销制度的观点显然是对相关法律关系解读不清的产物。
五、在新旧商标法体系下,“转让协议”在商标流转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羊老大”商标纠纷中,对北京公司有争议的受让行为之真实性和有效性难以作出确认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无法提供“转让协议”作为充分的受让根据。
根据笔者对我国商标转让制度立法变化的研究,我国的商标立法体系以2001年12月1日为界对商标转让法律关系设立要件作出了重大修正。此前,我国的商标转让核准制度十分简单,只要求由受让人单方办理并提供转让申请表即可,而不要求提供任何“转让协议”。
在1983年3月10日国务院首次颁布的商标法《实施细则》中规定,“申请转让注册商标的,每一个商标申请应当交送转让注册商标申请书一份,并交回原注册证。经商标局核准后,将原证加注发给受让人,并予公告”;此后,国务院于1988年和1993年对该《细则》进行的两次修订中均保留了转让人对原《商标注册证》的“交回”制度和商标局在原《商标注册证》中“加注”后发给受让人并公告的制度;但到1995年第三次修订《细则》时取消了对原证的“交回”和“加注”制度,仅规定“申请转让注册商标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向商标局交送《转让注册商标申请书》一份。转让注册商标申请手续由受让人办理。经商标局核准后,发给受让人相应证明,并予以公告”。可见,国务院关于商标管理的行政立法在防止“盗转”方面实际上存在着制度性倒退的情形。但商标法在2001年10月27日修订时在商标转让法律关系的设立要件方面有了重大的制度性变革,增加了“转让注册商标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签订转让协议,并共同向商标局提出申请”的规定。可见,转让商标既要有转让协议,又要共同申请。
但是,由国务院颁布并在2002年9月15日起施行的《商标法实施条例》却并未充分注意到这一立法上的重大变化,仍然原文“抄袭”了旧商标法在1995年第三次修订版中的规定,仅只是照旧规定商标转让“由受让人办理”,而没有按照新商标法的要求设置“双方共同办理”并提交“转让协议”等核准要件。在商标转让核准的实务中,国家商标局亦只注重《条例》这一小法而忽视了商标法本身的严格规定,使商标法在事实上被下位法架空。应该说,我国商标行政立法的上述严重疏漏在导致类似本案纠纷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制度性瑕疵。笔者建议,国务院应当对商标法《实施条例》尽速进行修订,以便在商标转让中将新商标法关于“转让协议”和“共同办理”的制度性要件落到实处。
六、商标权属争议和注册争议是否适用诉讼时效或除斥期间制度?
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当解构商标权的法律构成要素。商标权是由商标著作权(无论是平面商标或是三维立体商标均受著作权法保护)和商标行政许可权共同结合的产物,无论商标是否获得注册,商标所有人必然享有该商标的著作权。获得注册后将进一步享有具有专属性的商标行政许可权,这是授益行政行为在民商法领域的一种法律表现形态。其次,注册商标权的内容除了商标行政许可权外,尚有对商标著作权中的复制权和署名权的行使。由于复制权的权利期限要受50年保护期的限制而署名权则可永久性受到保护,故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商标权属争议不存在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法律空间。加之,注册商标权是依许可和依登记而产生的权利,类似于特许物权,这种类物权的属性完全排除了时效制度的适用可能(涉及索赔权除外)。他人对商标的侵权占有和使用不能因时效的经过而合法化,否则即等于保护侵权占有。即便是在权属争议中,争议各方在任何时段都有权提起确权之诉,故亦不可能存在适用时效制度或除斥期间的法律空间。
但在商标注册争议中则完全不同。由于注册争议解决的是在先权与在后权的冲突问题,因此在先权人如果无限期地怠于主张权利的话,当然没有给予其永久保护的必要。因此,商标注册争议必须要受到相应的除斥期间或诉讼时效制度的约束。例如,当异议方之商标为非驰名商标的则应适用5年的除斥期间制度,但异议方之商标构成驰名商标的则不受该5年期间的限制,但应当受民法20年最长诉讼时效的限制。在司法实务中的关键是对某一纠纷到底系商标权属争议或是注册争议作出正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