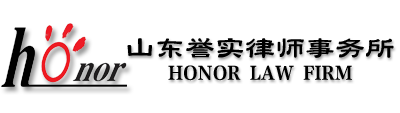| 关键词: 金融法;金融监管法;比较研究;研究方法 |
| 内容提要: 金融监管法是金融法体系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对金融监管法进行比较研究时,应首先遵循比较研究金融法的一般方法,即将所有主权国家下辖的各个法域归纳为若干相对独立的金融法体系,然后再选取恰当的衡量标准。由于破产制度是金融法的基石,各金融法体系在破产制度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它们在破产抵销、担保权益和商业信托等领域也有着不同的做法。金融监管法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存在和发展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并且各国金融监管制度在诸多方面存在一致性。因此,对金融监管法进行比较研究时,还应运用一些的特殊衡量标准,包括法律制度的刑法化程度、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及金融活动的自由程度等。实践表明,金融监管法的发展和演进深受各种历史因素和重大金融风险事件的影响。 |
| 一、当代世界各个法域概况 目前,世界大家庭共有193个主权国家,东帝汶和黑山是两个最新的成员。这些主权国家下辖大约320个法域(jurisdictions),既包括像中国和巴西这样的人口和领土大国,也包括像太平洋岛国纽埃这样的袖珍国家。 许多国家存在多个法域。例如,美国有51个法域(含哥伦比亚特区),加拿大有11个法域;澳大利亚有8个法域,英国有7个法域。如果不局限于金融监管法,而是就金融法的整体而言,判断是否构成独立法域的标准在于该地区的法律是否存在特殊之处,从而值得单独研究。当然,这一标准也是相对的。例如,墨西哥的法律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法律截然不同,而在拿破仑体系(Napoleonic group)、英国普通法体系(English common law group)或者美国普通法体系(American common law group)内部,许多国家的法律却相差无几。在加拿大和美国等大型联邦制国家里,这种趋同性更为明显。尽管如此,这些联邦制国家的各个法域仍然各有特点,有必要区别对待。从法律体系方面来看,澳大利亚实际上是一个单一的法域,由多个州组成的瑞士和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的巴西也都是如此。 如果将金融法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特别是以破产制度为标准来看,当今世界可以划分为大约320个法域。但是,金融监管法却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这样,研究对象的数量实际上不足200个。当然,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看法。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联邦制国家里,各法域的金融监管法基本趋同,但也存在差异。就本文而言,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关注美国各州以及加拿大各省金融监管法之间的差异,这两个国家分别被视为单一的法域。 二、各种金融法体系 金融监管法是金融法体系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就金融法整体而言,当今世界所有的法域可以被划分为8个主要的体系,即美国普通法体系(American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英国普通法体系(English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拿破仑体系(Napoleonic jurisdictions)、罗马-日耳曼体系(Roman-Germanic jurisdictions)、民法与普通法混合体系(mixed civil/common law jurisdictions)、伊斯兰体系(Islamic jurisdictions)、新兴体系(new jurisdictions)以及其他一些独立的法域。 美国普通法体系大体上包括美国各州以及美属萨摩亚、波多黎各和马绍尔群岛等另外10个较小的法域。 英国普通法体系涉及84个法域。如果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适用普通法的各省分别视为一个统一的法域,那么英国普通法体系共有68个法域。具体地讲,归属于这一体系的法域有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英格兰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印度、爱尔兰、以色列、马来西亚、新西兰、尼日利亚、英国北爱尔兰地区、巴基斯坦、新加坡、加勒比海地区众多岛国、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众多国家以及遍布全球的众多群岛地区,也包括孟加拉国和缅甸等其他法域。此外,这一体系还包括开曼群岛、巴巴多斯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以及土克斯-凯克斯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 拿破仑体系覆盖了82个法域,包括阿尔及利亚、比利时、巴西、埃及、法国、希腊、意大利、卢森堡、墨西哥、葡萄牙、西班牙、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和拉丁美洲地区的许多国家以及海洋中的一些群岛地区。 罗马-日耳曼体系有大约31个法域,包括奥地利、捷克、丹麦、芬兰、德国、韩国、荷兰、波兰,俄罗斯、瑞典和瑞士。本文将另外11个法域从这一体系中独立出来,划归下述民法与普通法混合体系。 民法与普通法混合体系涉及17个法域,且构成较为复杂,包括中国大陆地区、日本、英属泽西岛、列支敦士登、巴拿马、加拿大魁北克省、英国苏格兰地区、南非和中国台湾地区。 伊斯兰体系包括阿富汗、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也门等8个法域。 新兴体系有时也被称为转轨体系(transition jurisdictions),其成员主要是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通过推行法律改革,取消了国家对企业的经济控制,重建了私人财产权利体系,确认了市场经济原则。这一体系包含了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老挝、马其顿、蒙古、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等19个法域。 基于种种原因,部分法域未被划归为某一体系。这些法域包括南极地区、古巴和朝鲜等。 虽然我们能够将当今世界的所有法域划分为8个法律体系,但如果采用一种更为粗线条的方法对这些法域进行梳理,实质上可以将它们进一步整合为三个规模较大的法律体系,即起源于英国英格兰地区的盎格鲁-美利坚普通法体系(Anglo-American common law group),起源于法国的拿破仑体系以及主要起源于德国并在荷兰、瑞士等国家得到重大发展的罗马-日耳曼体系。大体上讲,上述三个法律体系下辖法域数量的比例为40:30:20。 三、衡量标准应当具备的条件 为了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必须选取恰当的衡量标准。这些标准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首先,应当对法律体系存在重大影响,不能过于琐细或者拘泥于细枝末节的问题;其次,比较研究的结果必须合理精确,这就要求必须获取充分的资料。那些与一般传统和文化有关的衡量标准难以把握,或者难以保持相对固定,因而无助于对金融监管法进行比较研究。再次,必须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在化学实验中,使用石蕊试纸能够测定试剂的酸碱性;在天文学上,根据外环空间电子的数量可以判断磁场的强弱,根据红移的幅度能够推测天体退行速度及其与地球之间的距离。与之类似,用于对金融法进行比较研究的标准也应当能够揭示金融法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从而具有合理的代表性。最后,衡量标准在数量上应当少而精,从而能够保证比较研究的任务不会过于繁重。 运用衡量标准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大体上可以被分解为以下三个步骤:首先,了解法律制度的内容,即法律条文是如何规定的;其次,判断这一法律制度在实践中的重要性;最后,分析上述法律制度在有关法域的执行、实施或者贯彻落实的情况。 就第一个步骤而言,为了了解法律制度的内容,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精确的资料,而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并且,也很难保证所有的资料都准确无误。在对金融监管法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情况尤为如此。金融监管制度的具体规定错综复杂,这使得对各法域的金融监管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结果难以达到预定的准确性标准。 第二个步骤是判断法律制度的重要性。这项工作的难度更大,而且也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有人主张,可以根据一些相关的信息作出判断。但是,两个事物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就必然存在因果关系,这一点世人皆知。例如,就基本的物质生活水平而言,在同属某个法律体系的不同法域之间比较,有的比较富庶,有的则极度贫困。因此,法律体系发达与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更不用说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了。 最后一个步骤是对当地法院和行政机关贯彻执行特定法律制度的情况进行评价。这项工作非常简单,因为那些前沿学者往往对这些情况耳熟能详,官方和非官方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情况表明,富庶的国家往往拥有良好的法律基础设施(legal infrastructure),而贫困的国家正在疲于解决温饱问题,在这方面无力投入大量的资源。并且,在那些贫困的国家,政府往往执政不力、操控民意或者独裁专制。 对金融法进行比较研究的前提是尽可能地总结出一套国际通行的法律制度。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需要以一丝不苟的态度,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细致入微地进行分析。任何一项客观的统计分析工作都应做到这一点。如果未能获取有关资料,我们就无法进行比较研究;如果无法进行比较研究,政策结论就很可能是错误的。在选取衡量标准时,应重点考虑某项法律制度对经济活动的重要意义及其功能和作用。尽管如此,在对那些已经体现了基本道德原则的法律体系进行比较研究时,我们也应当考虑它们是否尊重了具体的道德准则以及正义、公平等价值观念。不合理的处罚标准或者显失公平的法律制度会使市场参与者怨声载道、叫苦连天,对促进经济发展毫无益处。在金融监管法领域,情况尤为如此。这是因为,金融监管法既有功能性作用,例如通过资本充足率标准来确保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也有道德约束作用,例如禁止欺诈和不公平的交易行为。过分强调道德准则的作用往往会表现为一些最偏激的态度和最极端的做法。 四、用于比较金融法体系的标准 本文选取的、用于对各个法域金融法体系进行比较的标准都或多或少地涉及破产问题。这是因为,只有在破产的情况下,各个法域才不得不在能够持续经营的企业和无力维系的企业之间做出最艰难的选择。在其他情况下,这种选择的结果往往过于随意或者敷衍了事。此外,只有破产制度才能够促进真正的竞争,也正是破产制度才会激发最严重的不满情绪,导致最巨大的损失。另外,所有的衡量标准都有降低风险的作用,这就涉及了监管问题。金融监管法的基本精神就是防范风险,但本文选取的标准是针对整个金融法体系的,而不是专门针对金融监管法的。 有很多衡量标准可供选取。根据重要程度,我选取了其中三个关键性的标准,即是否可以实行破产抵销(insolvency set-off)、担保权益(security interest)制度的合法性及其范围以及是否允许建立商业信托。 选取抵销和轧差(netting)作为衡量标准的原因在于,它集中体现了各种价值取向的碰撞,交易规模也非常庞大。毫无疑问,破产抵销有利于债权人,不利于债务人。目前,全球金融市场日均交易额大约相当于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实行抵销和轧差能够削减95%以上的风险敞口。显然,这一标准满足了重要性的要求。在商业交易中,只要双方当事人互负债务,就可以实行抵销。然而,只有在金融市场中,破产抵销才能够大展身手。如果双方当事人均有偿付能力并可以清偿债务,那么抵销既不重要,也无必要。 担保权益在现代信用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可能发挥作用,包括商业银行为公司提供运营资金,项目融资,权益融资,并购融资,资产证券化,结算和清算以及衍生产品担保,船舶、航空器和其他运输工具融资等。在支付结算、项目融资、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这四个领域中,即使是保守地估算,全球金融市场担保融资的规模也极其巨大。例如,英国住房抵押贷款余额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 信托制度无论怎样概括,都不过是由受托人代委托人行使财产所有权,以维护财产实际所有人的利益,从而使信托财产可以不受受托人债权人的追索。信托安排最初被用于遗产继承和家庭财产管理等私人事项方面,这简直就是天才的创造。然而,与商业和金融信托相比,则不免有些相形见绌了。货物的寄存就是一种典型的信托安排。具体地讲,如果你将货物寄存到仓储公司的仓库,该仓储公司破产后,如果事先建立了信托安排,你就有权取回寄存的货物。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只要符合以下两个条件,就可以建立信托安排:其一,需要由中介机构或者资产管理人持有资产所有权,从而使之作为受托人能够管理委托人的资产;其二,在受托人破产的情况下,信托财产不受受托人债权人的索偿。 对于全球证券存管和结算体系以及资产管理服务而言,信托制度不可或缺。在受托管理担保权益和受托持有债券方面,信托制度也大有用武之地。在各类金融交易中,合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信托也是如此。选取信托制度作为衡量标准的理由是,信托安排涉及的交易金额非常大,并且在交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全球结算体系中信托安排的余额超过了全球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 上述三个衡量标准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的宗旨都是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不是保护债务人的利益。例如,根据浮动抵押安排(universal security interest),银行作为抵押权人可以就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优先受偿,而无担保的债权人将得不到任何偿付,能够行使抵销权的金融机构也能够保全自身的利益。又如,受益人将证券交给经纪人托管,若该经纪人破产,受益人可以在其他无担保债权人之前取回被托管的证券。 保护债权人的政策或者保护债务人的政策能否使债权人的利益最大化,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这一点也很难判断,因为无论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都可能另外对他人负有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应当保护哪一方债权人的利益呢? 除了上述学理分析外,实践中还出现了一种情况,即某些法域开始对提供商业贷款的一方,特别是银行给予特别保护,而不是保护借款人的利益。上述做法的理由或许是,银行是吸收公众存款的重要渠道,保护了银行的利益,也就间接地确保了公众存款的安全。在破产制度初创时期,法律对待债务人和债权人的态度泾渭分明,立法机关和法院不太可能以上述实用主义的方法来解释破产制度。因此,强调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做法很可能是因为人们不希望看到债务人破产后债权人将会遭受巨大的损失。 其他一些衡量标准也颇有价值。从表面上看,有的标准似乎是纯粹的技术性标准,实则不然。例如,与其他法律体系相比,普通法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即使面临破产的债务人已经通过多功能银行账户(comingled bank accounts)等途径掩盖了资金的来源并将这部分资金与其他用途的资金混同,债权人也能够追索逾期债权。在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资金已经被盗用、挪用或者被用于洗钱的情况下,债权人仍然有权追回。在法律上,这种追索债务的权利被称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unjust enrichment claims)。与其他衡量标准相比,这一标准涉及的交易金额极小,但却集中体现了破产程序的透明度(publicity)、破产财产的特定化(specificity)、破产优先权(priorities)以及对物所有权的分割权(in rem proprietary separatist rights)等与其他法律体系几乎是格格不入的法律原则和理论。因此,是否能够追根溯源地实现逾期债权是一个根本性的判断标准,能告诉我们某个法律体系属于普通法体系,还是属于民法体系。 五、运用基本标准比较金融法体系 运用上述标准进行比较研究的结果大体表明,一向较为保守的拿破仑体系对这三项法律制度均不认可,罗马-日耳曼体系认可其中一项制度,部分认可另外一项制度,盎格鲁-美利坚体系则同时认可了这三项制度;拿破仑体系基本上不允许实行破产抵销,担保权益制度相对不完善,也没有建立普通信托制度;罗马-日耳曼体系基本上建立了破产抵销制度,担保权益制度的完善程度介于拿破仑体系与盎格鲁-美利坚普通法体系之间。信托制度尽管遭到排斥,但也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从整体上讲,盎格鲁-美利坚普通法体系大都建立了破产抵销制度、全面的担保权益制度和普通信托制度。 就上述结论,有必要进一步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这种简单的三级分化大体上反映了三十年前的情况。如今,很多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当然,上述三个法律体系并没有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而是像汽车的风挡玻璃被石块击中后裂化为不计其数的碎片一样,各个法律体系也变得日益复杂,新的制度、新的例外规定以及新的特殊权利等层出不穷。于是,在单个法律体系内部,各种法律制度也体现出了鲜明的层次性。其二,如果认为上述三个法律体系的分化是由现实经济条件所决定的,例如,种种迹象表明,拿破仑体系与英国普通法体系有着截然不同的商业文化,那么这种看法就不免有失偏颇。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和第三大经济体德国分属罗马-日耳曼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法与普通法混合体系,而人均收入水平几乎是美国两倍并居全球首位的卢森堡却属于拿破仑体系。由此可见,法律体系的特点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在这些基础性法律制度方面,各法律体系之间差别甚大,这取决于历史因素而不是现实经济条件。此外,虽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经常被用来解释各国之间存在的种种差异,但上述各法律体系之间的分野却并非源于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是由法制理论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以及推动法制理论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所决定的。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催生了拿破仑体系,但这次革命却爆发于法国工业革命之前。这表明,拿破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由资本主义经济所主宰的,英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各种历史因素及其错综复杂的作用和影响决定了事物发展的历史脉络。上述三种法律体系都具有鲜明的代表性。然而,任何一种杰出的法律体系都必然会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精神作支撑。一旦这种精神开始发挥主导作用,特别是如果其中蕴含了合理的价值取向,那么即使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也不会轻易改变。上述三种法律体系都秉承了各自的历史传统,这是无法用现实发展诉求、经济环境或者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来解释的。 六、将法律和政治环境作为一种衡量标准 我们并不是用这一标准来衡量特定国家的政治状况。显然,在一些国家,政府执政不力、独裁,法律体系效率低下,法律也得不到有效实施。在那些衰败的国家,政治腐化、法治缺失,骚乱、犯罪和暴力活动此起彼伏。也有一些法域可能并没有出现上述极端的混乱情况,但执法体制软弱无力,国家机关人浮于事、官僚作风盛行,设立公司或者清收欠款耗时冗长,各种规费极不合理,公司监管部门以及其他政府主管部门的能力和工作效率差强人意。此外,在一些新兴体系国家,政府掌控着银行体系。结果是,政府可能会出于不正当的政治诉求而动用银行的资金,指令银行为一些有政治意义的项目或者为政治盟友提供资金。 本文的重点并不在于分析各法域的法律和政治环境。这些因素固然重要,且往往能够反映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但是,上述情况有目共睹,我们对此并不陌生,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此都有详尽的描述和分析。因此,对法律和政治环境进行比较研究并不困难。然而,客观地比较研究法律制度的具体规定及其影响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既不应泛泛而谈,也不应简单地进行归纳和总结。 即使在发达国家,不同法域的政治环境也不尽相同,贯彻执行法律规定的情况也千差万别。这既可能取决于人员、经费等各种执法资源的配置情况,也可能反映了金融监管机构对监管对象的态度,因为监管机构往往希望监管责任不要过于繁重,以便在配置监管资源时向大案要案倾斜。我们可以对监管机构采取执法措施的数量进行统计,但这些统计信息并不能够反映一项重要的指标,即违法行为和执法措施之间的比例关系。在某些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很少采取执法措施。这并不是因为金融监管机构怠于履行职责,而是因为市场参与者在进行金融交易活动时一贯高度诚信和自律。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国家由于尚未摆脱贫困和解决温饱问题,银行体系或者资本市场的资金来源匮乏,无法汇集资金用来促进共同发展。 无论如何,因循先例的理论、法律制度的精细化(codification)程度以及合同法中的原则等都不适宜作为比较研究金融法的主要标准。 七、各国金融监管法的共同之处 如上所述,就破产制度而言,不同法律体系的实践大相径庭。然而,各个法域的金融监管法之间却并不存在如此之大的差异。其中一个方面的原因在于,各主要法律体系都广泛地承袭了一种共同的传统。例如,在金融法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各个法律体系都对金融机构避免利益冲突、禁止掩饰利润、应当勤勉尽职、禁止利用秘密信息谋取私利等方面的受托责任(fiduciary duties)作了极其严格的规定。又如,各个法律体系都对虚假陈述(misrepresentation)的法律责任作了严格规定,涉及无过错的虚假陈述(innocent misrepresentation)、疏忽大意的虚假陈述(negligent misrepresentation)、故意和欺诈性的错误陈述(know and fraudulent misrepresentation)等。再如,对于利用虚假信息和以维护投资者利益为借口实施的欺诈性市场操纵行为,各个法律体系也都通过立法或者司法手段进行制裁。 总体上讲,监管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一个监管规则成文化、精细化并实现较高程度刑法化(criminalization) [1]的过程。以针对商业行为(conduct of business)和操纵市场行为(market manipulation)的监管规则为例,各个法律体系的金融监管法往往泛泛地规定,商业行为和操纵市场行为应遵守调整金融交易活动的一般法律规则,但不得以外包(contracting-out)的方式为非专业客户(unsophisticated customers)提供服务;对于重大违法行为,可以处罚款、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等。实际上,这体现了一种以原则为导向的监管模式(principle-based regulation)。 关于受托责任的一般规定并不涉及资本充足率等审慎监管事项,也不涉及会计准则方面的问题。目前,资本充足率制度的核心内容以及基本的会计原则都得到了各个法律体系的普遍认可,尽管在某些细节上,具体的规定还不尽一致。另外,就投资者保护问题而言,各个法律体系的金融监管法大都区分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设置了不同的监管标准,即批发市场适用一般的监管规则,而不适用较为严格的监管规则。 综上所述,各个法律体系的金融监管法都确立了一些类似基督教“十诫”(Ten Commandments)这样的基本原则,例如“禁止欺骗投资者”、“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客户”、“禁止欺骗银行”和“应当维持充足的资本”等。因此,在对金融监管法进行比较研究时,我们并不关注各个法律体系金融监管制度共有的内容。相反,我们应当探寻一些能够揭示种种重大差异的衡量标准。 八、用于比较金融监管法的标准 在对金融监管法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有许多衡量标准可供选取,它们的作用和相关程度各不相同。我们难以断定各法域金融监管法孰优孰劣。这是因为,虽然在金融监管法的某些方面,已经涌现了一些出类拔萃的研究成果,但只有依托大规模的团队,通过长期的跟踪研究,才能够收集到全球各法域的资料。令人遗憾的是,各法域金融监管法无不以维护自身利益为依归。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探求真理,客观、中立的态度至关重要,这是经济统计工作应当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 金融监管规则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相应地,对之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也应有所不同。我们不妨将其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本充足率等旨在确保商业银行偿付能力的审慎监管规则(prudential regulation);另一类是旨在强化受托责任的道德行为规则(moral regulation)。前者复杂、严谨,相对而言不受政治因素和道德准则的影响。相反,道德行为规则易受强硬派或者保守派、左翼或者右翼势力等政治团体的影响。 (一)监管机构的地位和独立性 毫无疑问,在避免多头监管、简化监管结构和控制监管成本等方面,监管机构的地位和独立性有着重要的意义。并且,监管机构的独立性还决定了监管机构是否能够审慎地做出决策。诚然,大多数国家都希望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那些采取多头监管体制(split regulation)的国家也希望能够有效地协调各种政策目标。虽然这种多头监管体制给监管和合规工作都带来了诸多不便,但这仍然不过是一个执法层面上的问题。在对金融监管法进行比较研究时,这一问题并不重要。 (二)法律制度的精细化程度 某些法域的金融监管制度高度精细化,而其他一些法域则更倾向于推行以原则为基础的监管模式。监管规则的精细化程度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在某些法域,人们可能会认为,如果监管缺位,必然会发生违规行为,因而应当加强对金融市场的控制和微观监管;也可能是为了提高法律的可预见性,以减少违规行为和处罚措施;或者是为了强化金融机构的合规意识;在某些情况下,就特定监管事项而言,也可能是不了解已经有了相应的监管规定。 建立和维持一系列过于精细的监管制度的成本以及确保合规的成本都很高。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这是一种无形的准入壁垒。因此,我们不应过分强调监管规则的精细化。在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应当重点关注金融监管制度内容,而不是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因此,监管规则的精细化这一标准固然重要,但仍然是一项次要的衡量标准。 (三)法律制度的刑法化程度 在不同法域,金融监管法的刑法化程度并不相同。这种刑法化可以通过建立明确的刑事处罚机制来实现,更多则是通过建立“准刑事的”行政处罚机制来实现的。上述两种模式的差别在于,前者过分强调刑罚的作用以及遵守道德准则的重要性,而后者则奉行道德准则的法治化原则,监管规则严厉但不过于苛刻。 在衡量金融监管法的刑法化程度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应当识别出哪些类型的行为属于犯罪行为。例如,利益冲突违反了关于受托责任的一般规定,这通常会引发民事法律责任;滥用未公开价格敏感信息的行为构成了内幕交易;通过巨额交易指令影响证券供求关系或者在交易日即将结束时通过巨额交易指令打压证券价格等行为属于非欺诈性的市场滥用行为(market abuse)。在识别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区分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后者往往以行政处罚为表现形式。 其次,应当分析刑法破除行业保护的力度。这方面的判断依据包括:法律是否要求由一个独立、公正的裁判机构取代监管机构下设的裁判机构;当事人依法是否享有指定陪审员的权利;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指控依法是否必须明确具体;法律含义不明时依法是否应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解释;被告人依法是否享有陈述意见和提起上诉的权利;依法是否实行无罪推定;是否做到了以合理怀疑作为定罪标准,而摒弃了根据可能性大小定罪的标准;是否遵守了不得自证其罪的原则以及犯罪嫌疑人是否享有沉默权;是否有严格的证据规则以及是否以存在犯罪故意或者过失为定罪条件,而不仅仅要求证明存在疏忽大意(negligence)。人类社会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确立了这些原则,它们不应被随意放弃。在很多发达国家,犯罪嫌疑人被剥夺了沉默权和不得自证其罪的权利,这是对上述刑事诉讼原则最严重的践踏。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根据这样那样的一些监管规定,违法嫌疑人必须如实说明其违法行为,并如实地回答问题。此外,就金融监管法制裁违法行为的方面来看,需要分析法律是否规定了强制性的检举和控告义务;应当检举和控告的范围除了重大犯罪行为外,是否还包括那些谨小慎微的违法行为。 最后,应当针对罚金、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以及确认合同不可强制执行或者宣告合同无效等处罚种类,比较处罚的轻重程度。同时,还应当分析通过司法救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护私权,以补充公权力救济之不足。例如,可以判令被告给予原告三倍的损害赔偿(treble damages)等额外的经济补偿,或者赋予原告一些特权等。这些特权包括:参与集团诉讼;允许审前调查(fishing expeditions)从而扩大获取证据资料的渠道;原告败诉不承担诉讼费用;根据判决结果确定律师的酬金等。就处罚的程度而言,英国金融服务局(FSA)对违法行为人处以罚款的最高金额曾达到1,700万英镑;在日本和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最高罚款金额数倍于英国的水平。但是,道听途说的信息或者个别事件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地收集资料。 (四)排外主义和保护主义程度 国家主义、排外主义、地区保护主义、沙文主义或者维护国家主权,无论用什么词语来概括此类做法,其程度都难以判断。 衡量排外主义或者地区保护主义的一个标准是,东道国是否限制外国金融机构在其境内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拓展业务,或者是否限制外国投资者收购东道国的金融机构。另外一个标准是,东道国是否允许外国企业在其境内发行证券,是否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向东道国境内居民投资者销售二级市场上的证券、集合资金投资计划份额等金融产品,或者提供财务咨询、金融资产管理、证券托管等方面的服务。 通常,通过法律规定限制外国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纯粹是出于保护主义的目的,可能是为了保护本国金融市场,保证将国内资金用于政府项目或者是为了防止政府失去对重要金融资产的控制权。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限制外国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会被认为是符合公共利益的,理由是外国法律对本国投资者的保护不足,且本国监管机构无法在境外执法。换言之,东道国金融监管机构无权在其他国家采取行政执法措施,因为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不认可或者不予执行外国行政机关作出的罚款决定或者其他行政处罚决定。上述理由常常被法律种族歧视主义理论(legal tribalism)用作“挡箭牌”,他们认为外国金融机构的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不如本国金融机构。 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方面,国际社会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欧盟在其内部市场上已经成功取消了大多数金融服务贸易壁垒,但是,要想让美国也完全开放其金融市场还需假以时日。尽管如此,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批发金融市场是完全开放的。这样,无论是本国发行人还是外国发行人,都可以向来自任何国家的机构投资者发行国际债券。对于共同基金以及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和证券托管等其他零售领域的跨境金融服务,市场并没有完全开放。 在日常的研究工作中,这一衡量标准极为重要。 (五)投资者受保护的程度 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各法域的金融监管法是否秉承了福利国家的理念,为投资者提供保护,并要求金融机构为自身过错承担责任。为此,应当详尽细致地研究特定法域的金融监管制度。其中,应重点关注的问题包括:是否建立了存款保险计划、投资者补偿计划及其上述计划的补偿范围;证券承销机构对招股说明书的错漏承担何种法律责任;投资者是否有权直接起诉上市公司的董事,或者只能起诉公司;基本的诉讼导向,包括是否允许集团诉讼,是否有原告败诉不承担对方当事人诉讼费用的规定,是否实行惩罚性赔偿,告知事项是否广泛,裁判机构是否值得信赖,是否允许根据判决结果支付律师酬金等;是否推行了替代司法诉讼的消费者监察专员计划(consumer ombudsman schemes),监察专员是否能够行使自由裁量权而不必严格拘泥于法律的规定,从而作出对消费者更为有利的裁决;是否通过合理的规定对投资者给予保护;是否针对金融机构、专业投资者以及其他投资者等各类市场参与者的特点,在净资本标准、公司准入、拆借资金利率以及参与投机性交易等方面,作了不同的规定。 在运用这一标准时,需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多。等到这项浩繁的研究工作完成时,研究成果恐怕已经过时了。 (六)金融活动的自由程度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参与者受到约束或者限制的程度。从根本上讲,这反映了国家通过金融监管制度对金融市场进行干预和控制的愿望,就像国家希望通过破产制度控制经济活动一样。 在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包括:获准从事金融业务的条件以及相关许可的配给情况;哪些金融业务必须经许可才能开展(这方面,除了证券托管等少数领域外,各国的做法极为一致);刑法化的程度;限制外国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程度;过于精细复杂的法律规定是否限制了市场准入,因为金融机构必须配备必要的资源才能够理解有关规定,还需要建立相应的合规部门;对服务外包的限制程度;批发金融市场上的证券承销机构是否无须承担招股说明书错漏的法律责任,证券经营机构是否也无须遵守强制性的商业行为规则等;是否通过精细化的法律制度实施微观监管;向监管机构上缴监管费以及向投资者补偿计划缴纳基金的情况;关于招股说明书、财务会计报告、宣传广告和会计政策等信息披露文件的要求;金融机构在接受现场检查、填报文件和配备合规人员等方面的监管负担。需要强调的是,比较研究的对象既包括有关监管制度的具体规定,也包括其实施状况。 在许多国家,金融服务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金融监管机构通常认为自己并不是发号施令的“君主”,而是为金融市场服务的“公仆”。批评人士认为,上述理念背后的真实目的是吸引各种商业资源,创造就业机会,增加财政收入,因而必然会导致监管标准的下滑。但也有人指出,这些国家崇尚金融自由,致力于提高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其根本目标是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繁荣,而不是压制金融活动。 九、美国与英国金融监管法的比较 美国和英国是两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它们同属盎格鲁-美利坚普通法体系,我们可以获得充分的研究资料。用上述标准对两国金融监管法进行比较后,我们发现,美国金融监管法的精细化、刑法化程度较高,对金融市场的准入限制较多;从投资者补偿计划、证券承销机构的法律责任以及基本的诉讼导向来看,对投资者的保护较为充分;但是,金融活动的自由程度较低。本文仅选取这两个国家进行比较。为了确保研究成果的实用性,需要扩大比较的范围,从而更全面地分析不同法域金融监管法的良莠优劣、远近亲疏。 十、影响监管法的各种因素 金融监管法的演进深受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有人认为,金融市场规模越大、越复杂,受到的监管也就越多。从表面上看,这种看法颇为合理,因为大型复杂的金融市场必然有大量的参与者,信用风险的集中度较高,风险敞口的规模也更大,这就很可能会引发较为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因而有必要实施更多的监管控制。对于像伦敦和纽约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而言,上述“规模论”的观点或许是正确的。此外,也有人认为,如果金融市场主要由少数有着良好商业操守的金融机构所主导,那么在该市场上就会形成一种集体文化,推行其独有的道德准则,要求所有市场参与者高度诚实守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如此,瑞士等一些国家至今也没有改变。在这些国家,金融市场中的道德准则并不是法律的强制性要求,而是在潜移默化地约束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这正是荷兰在十七世纪以及英国在十九世纪成为世界金融强国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当时的荷兰和英国根本没有金融监管法。因此,上述“规模论”的观点值得商榷。 从历史来看,金融监管法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统治阶级和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对货币借贷和投机性交易活动的基本态度。这些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因而对金融监管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违规行为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的情况屡见不鲜。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大量企业破产,违法违规行为暴露无遗,这必然会激起社会公众的强烈愤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影响金融监管法的重要因素之一。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事件 [2]对英国公司法的影响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密西西比公司(Mississippi Company)事件 [3]对法国法的影响也毫不逊色。另外,诸如十八世纪二十年代的高通货膨胀对德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4],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对美国监管制度的影响等等,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
| 注释: 【作者简介】 [英]菲利普·伍德 著 刘轶 蔺捷 译 菲利普·伍德(Philip R. Wood),是英国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Allen & Overy LLP)全球业务特别顾问,并分别兼任牛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伦敦大学皇后玛丽学院客座教授以及剑桥大学约克(Yorke)教席荣誉研究员。 刘轶,南开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站博士后,武汉大学法学博士。 蔺捷,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 2007年,英国斯韦特·马克斯韦尔出版公司(Sweet & Maxwell)先后出版了本文作者的九卷本系列专著“国际金融法律与实践丛书”,本文节选自该丛书的第一卷《国际金融监管》一书,经改编后发表于2007年10月出版的《资本市场法律学报》(Capital Market Law Journal)第2卷第4期。作者同意我们将本文译成中文,并推荐给中国读者。 [1] 刑法化是犯罪学上的一个概念,是指通过刑法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并规定具体的刑罚种类和量刑标准,从而使其成为刑事制裁的对象。在本文中,刑法化则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既包括刑法对金融犯罪活动的制裁,也包括行政法对金融违法行为的制裁。——译者注。 [2] 1711年,英国政府因战争负债而向一家名为南海公司的金融机构融资,并承诺按照6%的利率支付利息。此外,南海公司还获得了对南美洲殖民地的贸易专营权。此后,南海公司开始发行股票筹集资金,股本规模急剧膨胀。该公司的垄断利润吸引了大量投机资金,股价也扶摇直上。同时,南海公司的管理层还不断散步虚假信息或者制造种种假象,以迷惑投资者。受其影响,许多公司也凭借一些不切实际的题材竞相发行股票融资,并受到了投机资金的追捧。然而,南海公司的管理层很快就意识到,依靠正常的经营活动已经无法产生现金流,为了防止资金链断裂,必须发行更多的股票。并且,管理层暗中抛售了所持南海公司的全部股份。得知这一消息后,其他投资者也疯狂地沽售手中的各种股票,进而引发了一场严重的股灾。后来,直到1725年英国政府一直禁止任何公司发行股票。近一个世纪以后,英国经济才逐渐恢复。——译者注。 [3] 1715年,法国刚刚走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的阴霾。当时,国民税负沉重,国库严重亏空,货币大幅贬值。金融家约翰·劳(John Law)为法国国王路易斯十五世设计了一套平抑经济的方案,即成立一家银行回笼金属货币并发行纸币,纸币可以按照发行时的价值兑换金属货币。这套方案行之有效,也使约翰·劳赢得了法国政府的信任。1717年,约翰·劳收购了濒临破产的密西西比公司,并以之吸收合并了发行纸币的银行。在殖民地贸易、代征税款、铸造金属货币等方面,密西西比公司先后获得了多项特权。高额的垄断利润以及购买股票获利后的“羊群效应”使得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成为投机资本竞相追逐的对象。该公司则大量发行银行券为这种投资行为提供资金,进一步推高了股价,使之比最初上涨了20多倍。然而,这种没有以金属货币为基础的银行券几乎一文不值。不久,由于银行券的发行量过大,货币贬值的压力开始显现出来。得知密西西比公司的管理层已经暗中抛售了股票的消息后,公众投资者的信心遭受巨大打击,公司股价也几乎是直线下挫,很多百万富翁顷刻间变得一贫如洗。密西西比公司事件使得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经济走向萧条,也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诱因之一。——译者注。 [4]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筹措战争经费,德国政府宣布停止以纸币兑换黄金,以便货币的发行规模不受黄金储备规模的限制。战后,为了扩大出口,德国政府有意低估本币币值,但却因严重依赖进口原材料和食品,推高了国内的物价水平,输入了通货膨胀。同时,德国政府也未能有效利用财政政策进行调节。结果是,德国的货币供应量短期内增长了四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希特勒则趁机逐步掌握了国家权力。——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