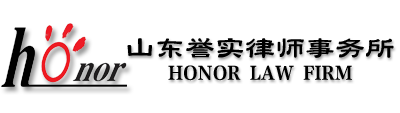Foundation and the goal of Judge Interpretation in Criminal law
【学科分类】刑法总则
【摘要】法官解释是一种客观事实,是指法官在办案过程中,一方面对法律规范进行理解、选择,明确刑法规范的含义,另一方面对案件材料进行剪裁,确定相关事实,将抽象的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案件的过程。法官解释具有主体的特定性,解释的多元性与地域性,结果的相对不确定性以及正义的终局性,其基础是社会的常识、常理、常情,目标是社会民众的认同。对法官解释的正确理解将有利于司法合理性的实现。
【英文摘要】Judge Interpretation is an objective fact, it refers to in the course of judging, the judge, on the one hand comprehend, select and choosing the law, on the other hand prune, confirm the evidence, and make the abstract law applied to the case. The Judge Interpretation has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special subject, diversity and regionality, relative uncertainty and is the final justice. Its foundation is “common sense, common reason, common situation”,its goal is People’s acceptability. Comprehend it correctly will convenient for the judicial rationality.
【关键词】法官解释;基础;民众认同
【英文关键词】Judge Interpretation; Foundation; People’s acceptability.
【正文】
一、无法回避的事实
立法者不是万能的,不可能完全预见将来发生的所有情况,法律一经制定就已经落后于社会,因此法律必须被解释,有法律就有解释,这一点已成为法学界的常识。当今大多数刑法学者也都承认刑法解释的必要性,各国也都构建了各自的刑法解释体制。我国由于受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响,建立的是以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的解释为有权解释的法律解释体制,这种体制虽然表面上能起到保持全国法律的统一性的效果,但却忽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只有法官才对法律是什么有最终的解释权。在司法过程中处理具体案件的法官同样拥有法律解释权,而且对于具体的案件而言,这种解释权甚至比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起到的作用更大,比所谓的“有权解释”更具有实效性。虽然这是一个既存的事实,但仍然有很多人对这一事实提出质疑,不愿正视。他们认为:首先,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以限制或剥夺人的基本权利为手段。为了保护人权,依据罪刑法定原则,法官不得对刑法进行解释,如果允许法官解释,将严重侵害人权。法官只能依据对刑法的有权解释机械的适用刑法。只有这样才能起到保护人权的作用;其次,他们认为法律并未赋予法官解释刑法的权利。我国法律只赋予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刑法的解释权,法官不是刑法解释的合法主体;再次,他们认为经过立法机关与最高司法机关解释的刑法已经足够明确,没有必要再由法官来解释,再由法官来解释则会对有权解释产生冲击,不利于国家法律的统一。这些观点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他们所说的法官机械适用法律,只是一种“工具性的法治”。他们未能看到法官解释是一个客观事实,不论我们是否承认,法官在司法实践中都将对刑法作出解释,法官解释都将存在。首先,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本身只是一种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对法律文本所做的一般性理解,具有抽象性,因此这种解释仍然只是一种需要法官再次解释的法律文本。其次,所谓“道可道,非常道”,那种认为思想总能表现为文字,文字与其所欲表现的事物之间总能对应的观点只是一种迷信。随着法治的发展,人们已经认识到,法律所利用的语言与数理逻辑及科学性语言不同,它并不是外延明确的概念,即使是较为明确的概念,也仍然经常包含一些本身欠缺明确界限的要素。同一用语在不同的法律,有时甚至在同一法律,同一法条中,都有不同的适用方式,不同的意义。法律的意义只有在与案件事实的交流中才能释放出来。例如我国刑法中的猥亵妇女儿童罪中的“猥亵”一词,在强制猥亵妇女与猥亵幼女的情况下,只能是性交以外的行为;而当对象是幼男的情况下猥亵却包括性交的行为,即已满16周岁的妇女与幼男发生性交的行为,也构成猥亵儿童罪。其次,法条中的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是不可避免的。如“猥亵”“侮辱”“歧视”等词,达到何种程度叫做“猥亵”?达到何种程度叫做“侮辱”?怎样才算“歧视”?这些词的含义可能由于地域,风俗习惯,思想开放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不通过法官根据具体案情来判断根本就不可能适用。虽然对于上述法律模糊的地方已有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但是没有一个解释可以主张它是终局的并且——可适用于任何时间的——“绝对正确的”解释。它绝不可能是终局的解释,因为生活关系如此多样,根本不能一览无遗,再者,生活关系也一直在变化中,因此,规范适用者必须一再面对新问题。 [1]可见法官解释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法律适用的必经阶段,机械的适用法律,没有法官的合理解释任何法律都将成为恶法。对于这一事实我们是采用“鸵鸟战术”回避它,还是正视它,对其加以规范化、合理化更好呢?结论不言自明。
二、法官解释的概念及其性质
(一)何谓解释
我国刑法学界一直认为“刑法解释就是对于刑法规范含义的说明” [2]或认为“刑法解释即对刑法规定含义的阐明”。 [3]这是一种典型的静态的解释观,认为解释是使法律文本中有疑义的文字意义变得可以理解。这种刑法解释观的产生源于限制司法权,禁止法官解释法律的传统。由于欧洲大陆独特的司法传统,以及在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法官阶层的反动作用,导致了人民“对法官的不信任”或者说“对法官专权的恐惧”。 [4]在当时这种社会背景下,反对司法专权自然成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革命成功后,资产阶级依然害怕他们的权利与自由会受到司法专权的侵害,因而当时卢梭、孟德斯鸠等思想家提出社会契约论,三权分立理论,认为立法、司法、行政权必须分立,只有对权力进行严格的限制才能保证民众的权利不被国家权力所侵犯。贝卡里亚更是认为“刑事法官根本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力,因为他们不是立法者”,“法官的法律适用过程就是进行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大前提是一般法律,小前提是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结论是自由或刑罚。” [5]在这种解释体制下,法官不能将其自己的见解带入法律之中,法官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只是机械的适用法律的工具。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逐渐认识到这只是思想家们所描绘的一个美丽的神话。司法的过程决不仅仅是简单套用三段论式的过程,法律的精神必须依靠法官结合具体事实灵活运用才能得到体现,正义才能得以彰显。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言“法不只是评价性的规范,它也将是有实效的力量,而从理念王国进入现实王国的门径,则是谙熟世俗生活关系的法官。正是在法官那里,法才道成肉身。” [6]
正因为对这一点的认识,现代外国法学理论中对法律的解释(interpretation)强调的是解释者与解释对象的相互作用,强调解释者对解释结果的影响,强调解释者内在的理解被解释对象的过程,而不是解释者向其他人说明自己理解的外部动作。 [7]强调解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解释者必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弥补法律的不足,通过对法律精神的理解而赋予解释对象更加丰富的内容,从而实现具体的正义。“只有规范与生活事实,应然与实然,彼此相互对应时,才产生实际的法律:法律是应然与实然的对应。” [8]因此,我国有学者认为,法律解释的对象应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本文”的成文法律,另一部分就是经过解释主体选择,并与成文法相关的事实,包括事件与行为。 [9]
(二)法官解释的概念与性质
1、法官解释的概念通过对解释概念的分析,笔者认为,所谓刑法中的法官解释,是指法官在办案过程中,一方面对法律规范进行理解、选择,明确刑法规范的含义,另一方面对案件材料进行剪裁,确定相关事实,将抽象的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案件的过程。司法者的任务就是目光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将法律规范与现实发生的事实相对应,从而彰显正义,实现法律的目的。“对法律规范进行理解、选择,决定刑法规范的含义”是指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在凭直觉对案件做出初步判断之后,寻找与其初断结果最相近的法条,然后通过对各法条的理解、选择,最终得出与案件事实最相符的法条。例如:王某得知李某随身携带着刚从外地收回的货款5000元,于是便请李某喝酒,李某以为王某确实想跟自己喝酒散心,便随王某一起来到“便宜坊餐馆”。王某故意叫了高度烈酒把李某灌醉,然后装着扶李某回家,路上王某趁李某酒醉不省人事,将李某装有5000元现金的腰包拿出,对李某说:“我叫出租车送你回家。”叫了出租车并用腰包中的现金付了车费,嘱咐司机将李某送回了家。事后,李某发现货款丢失,遂向公安机关报了案。面对这一案件,法官凭直觉会发现这个案件可能是盗窃,或者是抢劫,也有可能是侵占,这时法官就需要对这三个可能的罪名进行仔细的研究与比较,他会发现抢劫罪的规定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王某的行为可能就是该条中所规定的“其他方法”。通过对法条的理解、选择,法官得出了最适合于该行为的法条。
“对案件材料进行剪裁,确定相关事实”。是指法官在对法律规范理解、选择,决定的同时,另一方面法官也将对该案件事实进行斟酌与筛选,将与定罪量刑无关的事实剔除,最终确定对案件的最终裁决有用的事实。仍以上述案件为例,本案中王李两人在“便宜坊餐馆”喝的酒,喝的什么牌子的酒,坐出租车回家,这些都是与定罪量刑无关的事实,属于剔除之列。而犯罪嫌疑人王某得知李某随身携带着刚从外地收回的货款5000元,用酒将李某灌醉,李某不省人事等事实则与定罪量刑有关,因此应当保留。最终法官通过抽象的司法推理与法律适用,对案件做出判决,使抽象的法律规范在具体案件中得以实现,彰显正义,实现刑法的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目的。
2、法官解释的性质作为一种事实存在,法官解释具有如下性质:主体的特定性。法官解释强调的是法官在具体办案过程中对法律规范的适用过程,因此,其主体只能是法官。这一点不同于“适用解释”,后者强调的是法律在适用过程中对法律的解释,其外延比法官解释要广,在刑事司法过程中,适用解释的主体包括法官,检察官,侦查人员,律师等等多种参与司法过程的人员而在法官解释的过程中,法官的解释权是核心,是最终的有权解释,因此必须对这一主体的解释权加以特别关注。法官解释中的法官指的是参与案件决策的所有成员,不仅包括具体负责案件的合议庭成员,也包括疑难案件中参与决策的审判委员会成员。解释的多元性与地域性。由于法官解释的主体具体到各个办案的法官个人,因此,法官解释必然因办案法官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结果。对同一刑法规范,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对同一事实,不同的法官也可能做出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判决。不同的办案法官可能因为专业水平、个人性格、个人经历等等因素的不同而得出截然相反的结果。不同的地域也可能因为各地的风俗习惯、经济水平、社区观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对于这一点,不仅在具体的判案过程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是在抽象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也有所体现。如我国刑法第九十条关于民族自治地方刑法适用的变通规定正是出于对这一情况的考虑而设定。同样,对于盗窃罪的数额规定依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具体设定,也是因为地区间的差异而做出的变通规定。结果的相对不确定性。虽然法律文本为案件设定了一个大概可以预见的结果,为案件的结果设定了一个大概的界限,但由于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抽象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将不可避免,在这一大概界限里面法官仍然可以自由裁量。因此,具体案件的结果就由于法官的个体不同而具有了相对的不确定性。法官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会受到情绪的影响,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同一个法官,对于同一个案件,可能仅仅因为审理案件时的心情不好,而将被告重判个一年半载;或者因为心情好,而将被告少判几年。有人曾对法官的个人经历对于案件审判的影响做过调查,发现通常情况下凡是自己或者家人亲属等遭受过犯罪或者不法行为侵害的法官,在工作中如果碰到同类案件时一般都会受到该经历的影响,而对被告人判处稍重的刑罚。正义的终局性。决定什么是真正的现行法者乃是司法裁判。 [10]作为司法裁判的做出者,对于法律的最终效力,法官无疑是最具发言权的。美国联邦大法官杰克逊也曾说过:“我们是终审并非因为我们不犯错误,我们不犯错误仅仅因为我们是终审。” [11]司法是正义的最终保障,是现代社会的最后救济力量。只有经过法官解释的并最终用于具体案件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法官解释因此而具有了正义的终局性。那么将如何保障法官解释的确定化、合理化呢?笔者认为,不论是设置何种规范细则对法官解释进行规制,首先都必须明确认识法官解释的基础与目标,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设置出合理的规范。因此,本文将着重对法官解释的基础与目标做一定的分析与阐述。
三、法官解释的基础——常识、常理、常情
常识、常理、常情 [i]是立法的基础。人不仅是一种追求目的(purpose-seeking)的动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也是一种遵循规则(rule-following)的动物。 [12]人类发展之初,人们处于一种茹毛饮血的蒙昧状态,纯粹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活。但随着群体化,社会化的发展,为了更好的生存人们之间开始互相妥协、忍让,人类逐渐发现了一些如何更好生存的规则,并学会传承与遵循一些有利于群体生存与发展的规则。这些规则的形成源于人类的“永不满足”的本性,为了满足这一本性,人类必须遵循这些规则,不得破坏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他们的行为必须限制在社会所能容忍的程度之内,这是他们长期的生存经验的总结。这些规则是人与人在社会交往中所形成的,是一定群体之内的共识,最初表现为道德,然后表现为法律。因此,法律——一种道德强制手段——无非是要将众多歧异的善恶观念统一起来,用一种需要满足模式否定其他需要满足模式。 [13]现代社会的立法,虽然表面看来是立法机关合意的产物,但事实上正如马克思所说“立法者应当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思的现行法律行为当中。”法律只是一种得到特定群体普遍遵循的社会规则,是对普通民众意志的一种肯定与规范化,法律的产生不可能脱离民众的常识,不可能违背常理与常情。因此,世界各国都异口同声的宣称,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这是现代民主主义的要求,立法就是作为民众的代表通过一定的程序将民众普遍认同的一般观念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使其具有规范性与国家强制性。常识、常理、常情是司法的基础。在司法方面,法官在判案时也必须以常识、常理、常情为基础。每个法官都可能分享他所生活的社区中通行的正确与错误的观念, [14]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法官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不可能不受社会普遍的是非观,价值观的影响。在判案过程中这种社会普遍的是非观与价值观必然在法官的思维与判断中得到体现。从这一角度来讲,常识、常理、常情事实上会在司法过程中得以体现。从另一方面讲,由于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法律的产生源于社会的常识、常理、常情,而法官的任务是运用法律来为社会定分止争,通过在司法过程中对法律的运用来体现人民意志。因此,司法过程中法官的判案基础也不能脱离常识、常理、常情,只有以常识、常理、常情为基础才能真正的理解法律,由此得出的司法结果才能为社会所认可,才能为社会所接受。常识、常理、常情在法官解释中的具体运用。法官是活着的法律宣示者,法官对于法律是什么有着最终的发言权。因此,从长远看来,正如埃利希所说:“除了法官的人格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保证实现正义”。 [15]也正因如此,很多国家都在宪法中规定:“司法人员必须依据良心来履行职责”。或许人们会觉得“良心”太抽象,不具有可操作性,但事实上对于法官我们只能如此要求。法律是规范性文件,只能对一般事情做出规定,很多具体案件仍然需要法官的自由裁量,在法律规定的自由裁量范围内法官完全有权对其进行任意解释。例如以大家最熟悉的故意杀人罪为例,我国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依据这一条的规定,法官可以在死刑与三年有期徒刑之间自由裁量,而且这种裁量除了法官的良知之外,几乎是没有限制的。此外,由于中国刑法还有减轻处罚的规定,即在法定最低刑之下裁判刑罚,在这种情况下,杀人罪的刑罚还可以低到三年以下。因此,法官如果不以社会的常识、常理、常情为基础来理解法律,不依据自己的良心来履行职责,那他完全可以“合法的”践踏人权,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间。
那么如何才能保证法官真正合理的运用法律呢?笔者认为,要保证案件的合法合理,法官在面对一个案件凭直觉做出初步判断之时,他就必须是以自己的良心或依据常识、常理、常情来做出的初步判断,他所做出的判断必须是他认为合理的,并且他有理由认为其他有正常智力和良心的人都可能会合乎情理的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他不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而是必须将自己的判断与社区中普遍的对这一案件的看法做出比较,只要是不违背法律的,他就不能置社会的普遍判断于不顾。如果一个法官以执法之名将自己的憎恶或信仰作为生活规则强加给这个社区的话,那么他就是违背法律的初衷,是彻底的违法。但这也不是所谓的“广场审判”,“网络审判”,法官凭直觉,依据社会普遍观念做出的判断还只是司法过程的第一阶段。民众的意见只是法官判断的一个参考因素,当社会对某一案件或群起而攻之,或为犯罪人呐喊请愿时,我们应当把这些作为衡量其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的一个因素。这时,法官不仅不应指责舆论干扰了他的审判权,相反却应该感谢舆论为其提供了衡量一个行为社会意义的重要标准。因为,如果一个判决不能获得社会舆论最低限度的谅解,这个判决肯定不是一个好的判决。而一个好的法官总不能将一个坏的判决结果的责任完全推诿给立法者! [16]
在第一阶段中,法官凭直觉对案件先做出初步判断,但这并不是“先判后审”或“先定后审”,因为在司法过程的第二阶段中,法官会将自己的初步判断与法律规定相结合,求助于法律文本,为自己的初步判断寻找适当的法律依据。在此过程中,法官通过对法律的考查逐步修正自己先前的初步判断,对初步判断进行制定法所要求的加工,使其成为符合国家制定法要求的“司法产品”。这一阶段是法律推理的过程,若按照法律推理主要就是三段论推理的观点来看的话,在这一阶段,法官不仅应当以常识、常理、常情为基础来理解法律,对法律进行合理解释,以保证作为“大前提”的法律的正确与合理,而且法官还必须保证作为“小前提”的事实问题也合法合理,只有大小前提都合理了才能使得出的结论为民众所接受,才能得到民众的认同。法律实证主义者所信奉的“法官是独立的,并且只服从制定法”,不只是错的,而且根本不可能实现。确信只从制定法接受判决标准,并且不将其先在理解带入反思之中的法官,实际上是最不独立的法官。 [17]法官不仅应受到法律精神,法律文本的限制,而且还应受到民众的监督。在司法过程中考虑民众的认同,不仅不违背司法独立,而且还是防止司法腐败的最好的防腐剂。
四、 法官解释的目标——民众认同
所谓民众认同 [ii],是指判决结果得到社会民众的认可,符合民众的基本的是非观、正义观,民众都愿意接受这一判决结果。民众认同一方面包括犯罪人的认同,判决结果做出来应当让被告人心服口服,感到判决的公正合理,而不是感到自己被冤枉,是因为自己倒霉而受到刑罚的处罚。另一方面是指其他社会民众的认同,要让其他民众感到犯罪人是罪有应得,判决结果是正义的彰显,刑罚是犯罪的应有结果。这样才能让民众对自己的行为具有预测可能性,从而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在民众中形成自觉遵守法律的规范意识。刑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来源于社会,也将回归社会。判决结果就是刑法回归社会的途径,当一个判决结果做出来时,如果全社会都认为这个判决是有失公平的,认为被告人受到了冤枉,那这个判决就是失败的,民众就会因此对法律规范产生抵触情绪,失去对法律的信赖。但这里的民众认同并不是指要求法官去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去曲解法律,去迎合那些非理性的民意,这里的民众认同是指经过民众的理性思考之后所得出来的合乎理性的结论,而不是受少数人错误引导所产生的所谓的“民意”。虽然成文刑法是正义的文字表述,但并不意味着仅仅根据文字就可以发现刑法的全部真实含义。事实上,不管是采取主观解释,还是采取客观解释,都不是单纯通过法条文字揭示刑法的真正含义。 [18]刑法的真正含义就在于体现正义,而何谓“正义”从古到今经过无数哲人的追索都未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笔者认为,究竟何谓正义不是你我说了算,也不是某一伟大哲人说了算,对于民众法益的保护,民众纠纷的解决,还需民众自己说了算。在这里,最大的正义即民众的认同,只有得到了民众的认同法律才能长存,民众才会自觉去遵守,社会也才能长治久安,这不仅是法官解释的目标,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
【注释】
[i]陈忠林教授认为“常识、常理、常情”,是指为一个社会的普通民众长期认同,并且至今没有被证明是错误的基本的经验、基本的道理以及为该社会民众普遍认同与遵守的是非标准、行为准则。
[ii]这里之所以用“民众认同”而不用周光权教授所倡导的“公众认同”原因在于: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其产生基础源于民众,因而其判决结果也必将回到民众之中去,必须得到民众的认可,用“民众认同”一词更能体现法律的这一特性。有关“公众认同”相关内容,请参见周光权:论刑法的公众认同,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95.
[2] 高铭喧,马克昌.刑法学(上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20.
[3] 王作富.刑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1.
[4] 陈忠林:刑法散得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57-158.
[5] [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2.
[6] [德]拉德布鲁赫.法律智慧警句集[M].舒国滢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36.
[7] 陈忠林.刑罚的解释及其界限[A].张军.赵秉志.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C].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40.
[8] [德]亚图.考夫曼.法律哲学[M].刘幸义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148.
[9] 陈金钊.法律解释的哲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56.
[10]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0.
[11] BROWN V.ALLEN,244 U.S.443,540(1953),Justice Jackson, concurring opinion.转引自苏力.送法下乡[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61.
[12] R.S.PETERS, The concept of Motivation (London,1959),p:5 转引自[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7.
[13] 张武举.刑法的伦理基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06.
[14] [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98.66.
[15]同注[14].6.
[16] 吴丙新.修正的刑法解释理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170.
[17] [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M].吴从周译.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6.
[18] 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