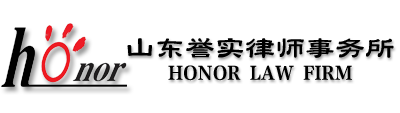|
|
王工:第一位律师代表
1988年的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里,第一次有律师入选,他们是安徽的王工、河南的梅养正、山西的晋辉和香港的廖瑶珠。而在大会会场连续4次即席发言的王工,成为那一届人代会最闪亮的记忆。当时的《红旗》杂志这样评价:“‘人大’被讥为‘橡皮图章’、‘表决机器’的现象已成为过去,人们心目中的‘两会’形象比以往高大丰满得多了。”
摄影◎黄宇
“宪法神圣”的呼喊
王工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已经60岁,临近退休。他记得评选前,1987年下半年,安徽省司法厅专门派了一个调查组,从合肥到蚌埠来了解他的情况。那时候律师都归属司法厅管理,当时在蚌埠市法律顾问处任职的王工,绝对算得上是蚌埠的“资深律师”。他于1978年“拨乱反正”后进入蚌埠市中院的司法科,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在蚌埠“坐堂办案”的律师,就只有他和夏桂涛。
王工也曾经当选过区里和蚌埠市的人大代表。对于突然到来的考查,并没有特别激动,用他的话说,是“以很平常的心对待”。虽然快退休了,但作为安徽省淮河修防局法律顾问,他手里还有许多案子要忙。几个月后,安徽省开人代会,王工高票当选。他在1988年3月来到了北京,走进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场。
他的当选很快成了新闻,这是全国人大代表名单里,第一次出现律师。
1988年,按照当时的大会规则,闭幕式上人大和“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分别结束时,大会的执行主席都会照例询问一句,是否有哪位代表对刚才的工作报告有意见。只是这个规则虽然设立了很多年,但基本上都相当于新报告开始前的过渡语。可1988年的气氛有些不同。王工到北京后,很快认识了香港的廖瑶珠和其他一些代表,也辗转听说,“廖瑶珠他们打算在大会上发言”。
王工很有些震撼,也暗暗下了决心,“香港的律师都要发言了,那内地的律师更不能当哑巴”。而且他觉得,自己和廖瑶珠他们比,有“地理条件上的优势”。他指的是座位,开会时候,王工的座位在“第三排靠左边的地方”。因为安徽团里的代表座位按笔画排序,除了一位姓丁的代表,就是他了,这是王工“占了姓名的便宜”。那时候各省代表团的位置,则是按拼音排序,从左到右,依次形成纵列。安徽团自然排在了最靠左边位置。王工记得,“当时钱其琛就坐在左边第一排”。
那是一种内心紧张而又期待的独自等待。那一年闭幕式上,政府工作报告结束后,大会主席习仲勋照例问了一句:“哪位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有意见?”王工马上举手站了起来,他就想赶在其他代表前面。他的发言是精心准备过的,他知道,这样的即席发言“只能讲几句,讲核心,戛然而止”。那一天,他用略带湖南口音的高亢嗓门说出来的话,令一代法律人备受鼓舞:“各位代表,请允许我遵循选民意愿,分别对有关报告的决议简要陈词。先对政府的三个报告的决议讲几点:第一,一手抓改革和建设,一手抓法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产生的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要做带头宣传宪法、遵守宪法,保证宪法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模范,我们的口号是:‘宪法神圣!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利益!’”
偌大的会场上,没有麦克风的发言,主席台上其实根本听不清楚。更重要的是,那天站起来即席发言的人,除了王工,还有其他人。在王工的叙述里,那也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场面,“记者们就在会场里”,“看到有人站起来发言,就奔着各自关注的目标围了过去”。闭幕式上,4份工作报告的结束间隙,一共有7人次的即席发言,而王工一个人就占了4次。
除了“宪法神圣”的呼声,他还有3次即席发言。在人大工作报告结束后,他说的是:“国家要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真正成为权力机关。”在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之后,他建议公开复查两个案子,“江西徐长根等7人故意杀人案”和“江苏省徐州电业局韩庄发电厂水资源费案”。在最高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之后,他又提出了“辽宁台安三律师案”。他说,“实事求是,是真理就坚持,是错误就随时修正”。
这令人讶异而又激动人心的时刻,被诸多媒体记录下来。比如《红旗》杂志写道:“代表即席发言……博得了广大代表热烈掌声,无疑是对这种民主行为的赞赏。‘人大’被讥为‘橡皮图章’、‘表决机器’的现象已成为过去,人们心目中的‘两会’形象比以往高大丰满得多了。”
议案最多的“中国一号”
通过1988年的即席发言,王工意识到了人大代表声音的分量。他提出的那3个案子,会后迅速得到了复查和纠正。“徐长根杀人案”中,被误判死刑的改判成了无罪,“水资源费案”的纠纷也得到了妥善解决。
尤其是“辽宁台安三律师案”,这案子当年很出名,彭真称此案为“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违宪事件”。辽宁台安律师王百义、王力成、王志双因为进行刑事辩护,1984年被违法逮捕,其中王力成先后两次被捕入狱,著名律师张思之为之辩护,但1988年此案还是没有得到纠正。还是王工的即席发言,推动了此案解决。《人民日报》两次头版头条报道了此事。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在全国维护律师职务权益经验交流会上也指出:“王工律师对‘三律师案’提出的意见,引起了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和高检重视。这件事已经解决了,教训是深刻的,要很好地记取,也说明了检察机关尊重律师,听取律师意见的重要性。”
只是在1988年之后,即席发言再也没能重现。王工回忆,因为从1989年的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始,“大会的规则就改变了”。“一府两院”和人大的工作报告结束之后,“执行主席再也不说有意见的代表可以发言了”。在他任期的5年里,全国人大会的规则还发生了其他改变,“以前是举手投票,后来就变成了按键,通过、反对和弃权3个按钮,电子计票”,这样一来,“在会场上根本不知道代表们心里都想些什么”。但王工始终对全国人代会充满期待,因为“人代会是我唯一重要的表达意见的机会”。
他为此做了大量案头准备。“每次会期,任务都很重。”如今已80岁的老人回忆起这些,还会不自觉地神采飞扬,“每次到北京,都忙着在宾馆写议案和建议”。除了奋笔疾书,王工还要在入住的宾馆里四处敲门,获取其他代表的签名,因为“议案要30个以上的代表签名,而建议、意见也需要几个代表签名”。他还是安徽代表团里的义务法律顾问,其他代表如果遇到什么法律问题,都会来找他。
5年全国人大代表任期下来,王工因为一人所提议案数量最多、议案序列第一而被媒体称为“中国一号”。他提出的诸多议案里,最出名的是1988年的“建议制定律师法”。王工回忆,这份议案和当时的大背景相关,“当时全国已有律师3万多人,律师事务所3000多个”,但“并没有专门的律师法,原来的《律师暂行条例》又过于简单笼统”。这份有31名代表签名的议案,排在当年的第219号。只是这议案距离1997年的《律师法》正式生效,还有9年的等待。另一个被频频提及的,就是他在1992年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的议案《依法主张1928~1946年日本侵华损害索赔权利》。
王工在全国人代会上,也多次显露法律人的专业素养。1991年4月,七届人大四次会议要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即将付诸大会表决的修改稿中第63条的内容是:“律师代理诉讼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代表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律师有伪造证据,行贿受贿,泄露查阅的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材料的,予以纪律处分、拘留,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王工仔细思索之后,提出建议“要求删除草案中的第63条”。他觉得,如果这条通过,在当时的执法环境下,律师很有可能陷入极大的被动,极其不利于中国法治建设。他还记得自己当时提出的理由:“一、这一条文内容属于实体法,不应放在程序法中规定;二、对律师的限制条文可以写进律师法,律师犯罪可以依据刑法论罪,民诉法可以不要这方面的内容;三、民诉法是程序法,它规定的应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操作程序;四、我国律师制度建立的时间不长,需要大力扶持,目前律师履行职务的困难较大,不少打击、迫害律师的案件没有得到处理,如果不删去这一条,将不利于律师制度的健全和发展……”他的建议在代表中引起了强烈共鸣。1991年4月6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修改草案)的审议结果报告中也“建议删去”“第63条”。同年4月9日,七届人大四次会议顺利通过了修改后的法案。
跌宕的命运
“我的名字叫王工,每次人大开会,我都能坐到最前面去,要举手发言的时候就占便宜了。但是工字上面不出头,所以我不能为士,成不了硕士、博士,当不了大学者;工字下面不出头,我也当不了官。”在蚌埠六中宿舍的窄小单元房里,80岁的王工还是那掷地有声的洪亮嗓门。
他只当了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没有用这身份为自己谋取任何特权,60岁照样退休,退休金如今也不过3000元。但王工对这些都不在意,60岁之前的他,已经遭遇过太多的命运坎坷,他唯一会感叹的是“时间太不够用”。动荡的时代剥夺了他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他能够专心投入一项事业的时候,已经50岁,于是总恨不得“1天当成20年来用”,退休后也无法闲下来。他这样总结自己,“50岁学法律,80岁尤执业”。他一直记得的是当年陶龛学校的校训,“血性”,做人要“诚和愚”。这也成为他毕生的信条。
命运的残酷考验,从他的童年开始。他本名兆晃,1929年出生于湖南沅江,童年和少年都在战乱中度过。八九岁时,就因为日本军队的轰炸,一家人逃难到湘乡。父母在他11岁时双双亡故,唯一的亲人只剩一个哥哥。他靠半工半读,完成了小学到高中的学业,而且在1947年考上了武汉华中师大教育专业。没有路费,他是和别人扒在火车顶上到的武汉,没有生活费,他就到湖南同乡会在武汉办的“克强中学”去应聘。这个18岁的年轻人,要“垫着板凳才能够得着黑板”。
王工在武汉迎来了1949年的解放。一夜之间,“蛇山上满山都是解放军”。这些军人“都很自律,宁愿睡在街上也不惊扰我们”。20岁的兆晃“受到很大的感动”,他决定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为了表达对革命的忠诚,他把名字改成王工,并且立刻放弃学业,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第12兵团,在政治部负责民运工作。后来12兵团一部组建人民海军,王工随即去了当时的海军基地青岛,几个月后,被派到北京任《人民海军》的编辑、记者。
可复杂的政治运动,再次改变了他的人生。1953年,面对历史背景调查,他因为“不能证明自己的历史是非常清白的”,只能被调任到基层的一个速成中学教书。直到1955年肃反,他才得以正名,被补授了少尉军衔。可1957年,“反右”开始,他又因为“没有老实交代个人问题”,调离北京,转业到安徽的蚌埠市委,在市委的《整风通讯》任编辑和记者。这工作没干多久,1958年的某一天,他就和一群人一起,突然被市委机关的人送去了公安局。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已经被定成“极右”分子,要被押解到合肥南边的白湖农场劳教。
“挖沟、筑堤,当年曹操屯兵10万,想开发白湖都没干成的事,被我们这些‘右派’和劳改犯干成了。”王工感慨。他在白湖农场一直劳动到1962年,他1963年被甄别平反,到蚌埠六中任教,与蚌埠的一名女工结婚,生育了两个孩子。可平静的日子很快又被“文革”中断,他这个“摘帽右派”,很快被关进牛棚,他的妻子也在“文革”期间死于医疗事故。
法律人的求索
王工真正有机会接触法律,已经是1979年。时任蚌埠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李奉山点名把他从六中调到中院。这一年,中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颁布,法制建设初露曙光。而王工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他可以过“有饭吃,有工作做的生活了”。
已经50岁的王工,要从零开始,学习做一名律师。他的学习,“从看法院张贴的杀人布告开始”。他也负责纠正案例卷宗中的文字错误,“当时的判决书老是闹笑话,错字不少,语句也不通顺”。在没有专业法律教材的年代,卷宗和判决书,都成了他的自学教材。他也很快成了在法院里“坐堂办案”的律师。那是个特殊年代,律师奇缺,最初蚌埠市就只有王工和夏桂涛两个人,后来也不过三五人。他们不用为案源发愁,案子会自动找上门。但也因为如此,律师们需要把各种案子“一锅端”,不管民事还是刑事,没有什么专业区分。遇到没有相关法律规定的案件,“只能抠政策,讲道理,甚至把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的司法经验、调解经验都用到法律实践当中”。
王工在蚌埠慢慢就有了名气,成为安徽省淮河修防局的法律顾问,接触到了一系列与水相关的麻烦案件,也成了那个年代著名的“水律师”,先后担任水利部、国家防汛总指挥部法律顾问,以及中国水法研究会理事。由于水利工程涉及民房搬迁、各个省份的水源分配等,纠纷多,官司复杂,当时律师比较少,“因为我胆子大,又说真话,找我的人特别多,就出名了”。
让王工一战成名的,是淮河流域著名的“二陈案”。1981年7月,安徽省公布实施《长江淮河河道堤防管理办法》,严禁在淮河干流和与之相接的河段堤防上盖房。正在泉河大堤上盖房的阜阳市居民陈子抗兄弟却置若罔闻,修起了7间砖房。事情逐步升级,市里责成公安干警强行拆除违章建筑。但二陈以老母亲的性命相要挟。事情闹到法院,一审判决限二陈于判决生效15天内无偿拆除,二审维持原判,但判决迟迟执行不下去。小小的案子,水电部曾发出专函,省委、省政府、省高院、省公安厅等15位省厅级干部,曾做过亲笔批示,省政府曾专门组织调查组前往阜阳催办此案,结果都没能解决。看完卷宗材料,王工的倔劲上来了。在调查取证后,他把自己反锁在省水利厅客房,据实以编年体形式写成《一宗破坏淮河的“胡子案”的调查报告》,送往北京。5天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批复,10天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也做出了批复。治淮工程中的这颗“硬钉子”,终于被拔了出来。此后泉河大堤相继出现190间违章建筑,也得到了彻底清理。
王工的足迹,随着他的案子,遍及各个江河流域。1989年退休之后的20年里,他也闲不住,陆续接案子,为一些特殊案件鼓与呼。他曾在80年代再婚,可这段婚姻去年意外地走到了尽头。老伴的亲生孩子都在国外,他们希望母亲能过去同住,而王工舍不下自己事业,他觉得到了国外,自己真的什么也做不了。老两口在平静协商后分开,再次孤身一人的王工,生活得像孤独的高龄独行侠。他挂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下当律师,律所专门为他在办公室里支了张床,在北京的时候,他就住在办公室里,而随着案子到了外地的时候,不用手机的他就变得行踪不定了。如今80岁的王工,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孤寂,他回过湖南老家,已经没有亲人的音讯,回到蚌埠,当年的朋友,或者不在了,或者反应迟钝。他自嘲,“也许现在独自坐火车的人里,我是年纪最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