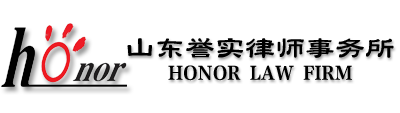9年前,(陕西)横山党岔镇枣湾村村民高怀堂的死亡,让同村贺玉山家族男子几乎全部身陷囹圄。
至今,他们中有的人已在看守所羁押超过9年,有的虽未终审判决但已坐满“刑期”,有的被一审认定无罪……
此案历经法院四次发回重审。期间,被告人翻供、证人“反水”的现象几乎贯穿始终。而办案人员和被害人家属则认为“案子没问题”。
9年前的那个傍晚,到底发生了什么?直至今天,真相依然模糊。
9年前的那个傍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一个人的死亡,一个被认为有罪的家族开始命运转折,男子几乎全部身陷囹圄。至今,他们中有的人已在看守所羁押超过9年,有的虽未终审判决但已坐满“刑期”,有的被一审认定无罪……历经法院四次发回重审,今天,真相依然模糊。而一群身陷其中的人,在经历了命运的过山车后,尚期待着最后的结局。
活了大半辈子,王宏仁说,自己保存最认真的,是在看守所里掉下的23颗牙。
掉落经年的牙齿,黑黄、难看,被王宏仁小心翼翼地裹在塑料袋里,压在窑洞炕上木箱的最下边。“我在法庭上喊冤时,也给法官看过。”他说。
这个57岁的男人,说起被当做杀人案嫌疑人关押的8年和拿到一审无罪判决时的经历,像孩子一样放声大哭。
时间回溯到9年前。家住横山县党岔镇王家洼村的王宏仁,还没戴上满口整齐的不自然的假牙。那时,小名旦娃的他,是村子里爱红火、喜欢往人前头去的“热闹人”。家里的窑洞虽旧了,娃娃们却有出息,大儿子刚考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二儿子学习也好,女儿就要上卫校了。他和妻子侍弄着家里的十多亩地。农闲时,坐不住,就走乡串户当货郎。
2001年春节后,农历二月二十六,货郎王宏仁和同村的王成华出门了。背个背包,装着针头线脑、线衣线裤、娃娃们用的铅笔本子等,在周围的乡村叫卖。早春风大,天冷,三四天后,两个人扛不住了,商量着回家。头一天晚上,他们在亲戚家住了一宿,第二天坐班车,傍晚时,两人在家附近的岔路口下了车,一个搭摩托回家,一个坐上了同村拉煤的三轮车。
坐三轮车回家的王宏仁,半路上看见一辆翻了的三轮车。司机受伤了,躺在地上呻唤,王宏仁认得那是姐夫同村的人,就帮忙把人送到上盐湾医院。这个医院条件不好,又等到鱼河医院的车来把伤员接走,他才和两个村民相跟着回家,已是晚上8点左右。
那一天是2001年的3月24日,农历二月三十。王宏仁记得那天晚上风大,没有月亮,自己回到家早早睡了。“做梦都梦不到,这一天成了我犯罪杀人的日子。”
卷入杀人案
那个傍晚,与王宏仁同镇的枣湾村人、38岁的高怀堂正经历着一场生死劫。13天后,高怀堂在医院抢救无效死去。死因被鉴定为“钝性工具多次打击头部致死”,公安机关认定其被殴打的时间正是3月24日。
王宏仁和高怀堂以前见过面,但很少说话。王的姐夫贺玉山与高怀堂同村,他去姐姐家“串亲戚”时见过。
3月24日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并导致高怀堂后来的死亡?9年过去了,这个疑问在经历了榆林市榆阳区公安分局侦破、榆林市检察院起诉,榆林中院和陕西省高院的四次一审、四次发回重审之后,至今依然是一个谜团。
但犯罪嫌疑一开始就直指贺玉山一家。
至今,没有争议的事实是:3月24日晚上,横山县党岔镇枣湾村的高怀堂被人发现倒在从榆林回家的路上。目击证人证明,当晚7时,高坐在路边。次日上午11点多,他被发现坐在300多米外的水壕中。“目光呆滞,问不答语(公安机关勘察笔录)”,有人从其身上找到电话本,打电话给其弟高怀伟,遂送到医院抢救。
还可以认定的是,高怀堂与贺玉山一家正“闹矛盾”,贺家当时正在寻找躲避在外的高怀堂。5个月前,高怀堂酒后跑到贺玉山家大撒酒疯。当时只有55岁的贺妻王宏英在家,高怀堂称要强奸王,王逃出家门,未遂。事发第三天,贺家儿媳妇向横山县公安局报了案。此后,高一直躲在外边,过年都没敢回家。
此前的3月22日,贺玉山的女婿朱继锋曾带着横山县公安局的干警,开车到榆林市找高怀堂,在高的弟弟高怀伟所在的饭店门口寻访,未果。两天后,高被打,4月6日,高怀堂死了。
3月27日,因案发地属于榆阳区,高怀伟向榆阳区公安局报了案。同时提供贺家人有重大嫌疑。
4月7日,榆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王海英在“重大刑事案件立案报告表”上签字,“同意列为重大案件”。从此,贺玉山一家包括族人、亲戚,开始命运转折。王宏仁作为贺玉山的妻弟,也被卷入其中。
4月29日,王宏仁被刑拘。比他早一天刑拘的,有贺玉山的兄弟贺占胜、女婿朱继锋、儿子贺彬。6月12日,朱继锋的表弟陈培峰也被抓。
他们5个人分别接受讯问,最后被列为“团伙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
3次供认有罪
王宏仁是在被抓5天后“交代”的。后来的庭审表明,一开始他就说了3月24日傍晚参与救人的事,证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但后来的讯问中,王宏仁“改口”了。
在榆阳区公安分局的讯问笔录中,王宏仁如此供述自己参与杀人的经过:“2001年3月24日下午,我到二姐(贺玉山妻)家,骑摩托回来时走到五娃(贺占胜小名)打石头的地方,听到五娃说,三召(朱继锋小名)诱上三板娃(高怀堂小名)了,准备引人,让在鱼河峁加油站等着。五娃让我一起去,我不去,后来我骑摩托送五娃到加油站,看到三召、彦娃(贺彬小名)等人打高。我还劝不要把人打死了……”
至于几个人怎么打的高怀堂,他也交代得很详细:“他们四人拳打脚踢了大约十分钟,三板娃就被打得没反应了。三召用左手在三板娃的脖子上卡着,三板娃也叫不出声。把三板娃打得睡在地上喘息,眼睛闭着了,因为天黑,我也没有看见三板娃有什么伤。”
在公安机关的讯问中,王宏仁先后“招供”了3次。这些口供,加上朱继锋、贺占胜等被抓亲戚的供述,后来提交法庭,作为他参与杀人的证据。
此后,在榆林中院的3次一审判决中,王宏仁被分别判处15年、15年、10年。
一直到2008年12月,经陕西省高院第三次发回重审,榆林中院第四次一审,王宏仁被宣告无罪。这次,法庭采信了鱼河医院的证明,当时的受伤者以及王成华等人的证言,确认他在3月24日参与救人,无作案时间。“那时,我实在被打得受不了,吼叫得厉害,他们把一块毛巾塞我嘴里,猛然用手一拉,3颗牙就拔松了,血直流。”2010年8月,王宏仁这样解释自己当初为什么会“招供”。
在后来的多次开庭中,王宏仁曾向法官出示自己掉落的牙齿。他说,他招供后才被送进看守所,此后,受损伤的牙齿开始脱落。2001年10月15日,第一颗牙掉了。以后,陆陆续续,满口牙几乎掉光了。
作为公诉人的榆林市检察院检察官罗岚,曾在法庭上目睹王宏仁“哭诉冤枉”这一幕。
8月20日,罗岚告诉记者,这个案子中,包括王宏仁在内的多名被告人,都曾称遭受刑讯逼供。“但我们进行了调查,包括出示公安机关的录像等,并没有发现刑讯逼供的证据。”
是否存在刑讯逼供,当年办案民警之一张某说:“我认为不存在。”至今,他始终认为案子是贺家人干的,“这没有任何问题”。
1800度近视,能否去作案?
王宏仁被认定没有作案时间。由此,一直“招认”坐王宏仁的摩托车去“打人”的贺占胜,同时也被宣告无罪。
在无罪判决下达前7个月,按照羁押一日抵刑期一日,贺占胜已“坐满”榆林市中院第三次一审判决的7年刑期。
“把我还多关了一天呢。”2010年8月18日,贺占胜说。原来,2008年4月27日,他就该“刑满释放”了。但当天是星期天,中院的法官没有来宣布释放他。当时看守所所长还专门给他做思想工作,让他不要“着忙”,晚上在11号监室,再睡一晚上。“我答应了。那天,所长吃啥,我吃啥,我要出去了,他们也为我高兴哩。”
可那一天真是度日如年。“儿子和侄女给我带了羊肉,在门口等我出来,结果多关了一天。我一夜睡不着,羊肉也吃不下去。”上午11点,法院的人来宣布了,贺占胜这才走出了看守所。
“出了看守所大门,儿子把我拉住了,一个没见过的女娃喊我一声‘爸’,原来是儿媳妇,已经怀孕4个月了。我当时就泪流满面。我被抓时,儿子才上初一,因为我,娃也失学了。”
他说,自己是高度近视,这么多年,看守所不许探视;开庭时别的被告还能看亲人一眼,自己呢,啥也看不清楚。只有一次,开完庭,儿子扑到跟前,喊他,他才算见了妻儿一面。
这个47岁的男人絮叨着:“出来那一天,兄弟姐妹,一家20多口人等我吃饭。我坐下第一句问‘妈呢’,四哥才说,我妈头年9月就没有了……”
贺占胜说,当年他被抓后,老母亲还曾去上访反映过。这次,他回到了7年没回的村庄,给老母亲烧了纸。
出来后,贺占胜去找了当年案件的代理律师吴文。第一次开庭前,律师会见,他曾在这个老律师面前跪下哭诉,说自己是被冤枉的。这次,他来见吴文律师,是想请律师为自己写一个国家赔偿申请。
“我眼睛1800度的近视。当时被抓后,我就给他们说,我近视这么厉害,天一黑就啥都看不清,如果被拉去打人,还不拖累人家?”贺占胜说。
被抓后的贺占胜,曾在公安机关先后做过8次供述,承认自己在3月24日那天参与“杀人”。
他说,事实上,3月24日那天晚上,他白天在村里打石头,晚上去同村的人家,商量买羊粪,要“奶”果树呢。“我们几个人拉话,出门时天黑透了,我眼睛不好,那家的娃儿还给我指着路回来的。”
5名被告当庭全部翻供
2002年5月,榆林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王宏仁和贺占胜被列为第三、第四被告。第一被告是朱继锋(贺玉山女婿),第二被告是贺彬(贺玉山儿子),第五被告是陈培峰(朱继锋表弟)。
检察院指控朱继锋、贺彬、王宏仁等5人,因私怨报复高怀堂,在高从榆林回家的半路上殴打使其受伤,并抛弃在路边,企图制造车祸假象,最终致高死亡。
2002年7月9日,案子第一次开庭审理。吴文记得,那天法庭上下“哭作一团”。
法庭上,5名被告全部翻供,称当初供述杀人,是因为公安机关“刑讯逼供,事实上根本没有作案”。“王宏仁喊冤的声音最大。”65岁的吴文说。当时,吴文是第二被告贺彬的辩护人。因案情复杂,代理此案后,他会见了每一个被告人。
吴文的刑辩经验丰富,做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至今,他还认为,“贺家人确实有嫌疑,但嫌疑也只能是嫌疑。法庭上,公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是他们作案”。
但公诉人也是有备而来。在吴文的印象中,8年前的那次庭审,控辩双方曾对证据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
吴文的当事人贺彬,是贺玉山的儿子,也是5名被告中唯一的“公家人”。贺彬当时是党岔镇的合同制干部。吴文的调查中,包括党岔镇人大主席王生利等多名证人,都证明3月24日当天,贺彬一直在镇上参与计划生育工作。当晚,在阳湾一个叫“得和禄”的小饭馆吃饭,晚上喝了4瓶酒。贺彬一直在酒桌上,晚上10点和大家一起回乡政府,无作案时间。“即使有作案时间,这5个人相距数百公里,地处山乡,要在当天聚集,必须有电话联络。他们是怎么联系的?”吴文质疑。
事实上,在2001年,手机还很少见。当时,朱继锋有个手机,贺彬有个传呼,其他人连固定电话都没有。案发后,公安机关调取了相关记录,也称“相关人员的手机通话情况,未发现有价值线索”。
吴文还发现,法庭上出示的证据全是书证。检察院指控的犯罪工具,包括作案时乘坐的吉普车以及打人用的棍棒、毛巾等,都没有。
而书证中,除了被告人自己的口供外,关键证词是一位“目击证人”孙长国的。孙称当晚看见朱继锋等人把高怀堂抬下车。但孙长国在4月26日作完证、离开公安局后,随即就向检察院控告,说警察控制他长达57个小时,并进行威胁、殴打,他才编造了自己骑自行车去买药、偶遇现场的情节。
尽管如此,法庭依然认为犯罪成立。
2002年9月,榆林中院宣判,认定5个人犯有故意杀人罪:朱继锋被判处死缓;贺彬无期徒刑;王宏仁被判15年;贺占胜13年;陈培峰8年。
宣判后5个人不服,提起上诉。陕西省高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
2003年9月,榆林中院再次作出一审判决,结果和第一次判决几乎一模一样。
5名被告人再次上诉,陕西省高院再次发回重审。理由依然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两次一审,两次发回重审,案件似乎陷入了僵局。2006年5月,检察院撤回了对5个人的起诉,发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
“5人团伙”变为“9人团伙”
当案子由榆林市检察院撤诉、退回补充侦查时,王宏仁、贺占胜等5名被告,已在看守所里度过了4年。
这4年里,贺家人一直没有停止过上访。
贺玉山曾担任枣湾村村支书近10年。案发时,他曾作为“主谋”被刑拘,关了两个月后,放了。因为女婿、儿子、弟弟、妻弟都被“关”了,时年51岁的贺玉山多次和女儿去北京上访,称公安机关“制造冤案”。2004年的一次庭审,贺玉山还曾出庭为弟弟贺占胜做辩护人。
一直到2005年12月,贺玉山也被当做团伙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刑拘。当初指控的“5人犯罪团伙”也变成了“9人犯罪团伙”。
正如当时的办案民警张某于2010年8月23日在电话中对记者所说:“这个案子起死回生还是一个和案件无关的人。”
据称,2005年12月,在内蒙古服刑的犯人辛起来,写信给榆林中院。辛称听和自己关在一起的白光军说,曾和几个亲戚在榆林把人打了,出了人命。白光军是朱继锋的外甥,2004年因抢劫和盗窃被判刑,在内蒙服刑。辛为“立功”,向法院检举。
公安机关把白光军带回了榆林,开始审讯。白光军很快就“交代”了,称曾经和朱继锋等人绑架了高怀堂殴打,并将其抛弃在路边。
白光军的“交代”中,除了他自己,还有另外3名参与者,即贺玉山、榆林下岗职工朱绪平以及邻村的孙世慧。这两人与贺家多少都有点沾亲带故。
在白光军的供述中,贺玉山在案件中扮演指挥的角色,带着一包木棍,在路边等待朱继锋开车会合,并共同参与殴打高怀堂。
白光军的供述被公安机关认为是“重大突破”。2006年7月,榆林市检察院第三次公诉,除了被告人从5个变成9个外,指控的事实也有了变化。以前指控5人在半路殴打高怀堂,变更成:朱继锋等人在榆林市内,劫持高怀堂上了一辆吉普车,另一部分人包括贺玉山、贺彬等在半路等候,两车会合后共同殴打高怀堂,并抛弃路边。
此次庭审,榆林中院认定9人有罪,作出判决。朱继锋从死缓改判无期,贺玉山被判13年,贺彬被判10年,王宏仁被判10年,贺占胜被判7年,其他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白光军此前因盗窃、抢劫已被判8年,实行并罚后,只决定执行刑期8年半,等于这次审判只增加了半年刑期。
“杀人被判半年,太不正常了。只能说明是警方实现了某种对白的承诺。”曾在第三次上诉中代理此案的律师在辩护中说。
事实上,宣判后,只有白光军表示服判,其余的8名被告人全部上诉。上诉后,陕西省高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再次发回重审。
此后,榆林市中院第四次开庭。这次,法院判决认为,王宏仁和贺占胜没有作案时间,宣告无罪。对其他的7名被告人,依然作出有罪判决。
而另外的被告人继续上诉。2009年7月,陕西省高院依然认为“事实不清”,再次发回重审。
尚未终审 6人“刑满”
2010年8月11日,朱继锋杀人案第五次启动一审程序。
而此时,除了朱继锋和贺玉山以及另案在身的白光军,其他6名被告虽判决尚未生效,但几乎都已服满一审判处的刑罚,“出狱了”。
王宏仁和贺占胜在放出来前后等到了一审无罪判决;而其他4名被告在走出看守所后,就开始上访。
贺彬从最早的无期徒刑,到第四次被一审改判8年。2009年4月27日,他服满8年“刑期”,走出了看守所,从34岁,倏忽已到42岁。
8年前,贺彬还是党岔镇政府的合同制干部。案发前,他刚被报上去转正的指标。在被关进去的那个春天,他的公务员证发下来了。8年后,他事实上已失去了这个曾梦想和盼望过的“公务员身份”。
被放出来的贺彬,一对儿女已长大。孩子当时因他被抓而失学,如今在外打工。唯一让他安慰的是,8年过去了,妻子没有离开他。“她知道我没有杀人”。
“当年我母亲被欺负后,我们都报警了,横山县公安局也很重视。如果想打死高怀堂,我们还会报警吗。再说我爸就我这一个独子,怎么会让我去干打人杀人的事?”这个自小被认为性格“软弱”的男人,闷闷地说。
失去工作的贺彬,如今在姐姐开的饭馆里帮忙。有点时间,就去上访。这个43岁的男人让记者看他手腕上的白色印记,说那是当年刑讯逼供留下的。
贺彬走出看守所后,几个当年的同事来看他,包括当年的镇人大主席王生利。王生利当时划片分管计划生育,是贺彬的直接领导。后调到横山县农业局工作。
2010年8月,王生利告诉记者,当时在乡镇,大伙儿一天到晚忙着抓计划生育,3月24日当天,做了5例计划生育手术,贺彬作为驻村干部,根本没时间走开。晚上,大家又一起喝酒,这些不仅有一起吃饭的7个人为证,还有饭馆老板、食客等作证。但不知为什么,法院最后没有采纳这些证据。
而唯一的“目击证人”孙长国则对记者说:自己倒霉,不知被谁提供给公安局,原本那晚在家里喝酒,被警察抓去让他作证,自小没进过派出所的他,被警察连打带吓,就编造说看见了现场。
案件进展情况
1.2001年3月24日,高怀堂被发现倒在路边,头部受伤。4月6日死亡。
2.2001年4月28日到29日,朱继锋、贺彬、王宏仁、贺占胜4人被刑拘,6月12日,陈培峰被刑拘。
3.2002年9月,榆林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朱继锋死缓,贺彬无期,王宏仁15年,贺占胜13年,陈培峰8年。被告人均上诉。
4.2003年4月,陕西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
5.2003年9月,榆林市中院第二次作出一审判决,内容和第一次判决基本相同。被告人又上诉。
6.2005年12月,陕西省高院再次发回重审。
7.2006年1月,榆阳区公安局拘捕贺玉山、朱绪平等4人,认定“9人犯罪团伙”。
8.2006年5月,榆林市检察院以证据不足撤诉,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9.2006年7月,榆林市检察院以“9人犯罪团伙”提起公诉。
10.2006年10月,榆林市中院作出第三次一审判决,判处朱继锋无期徒刑,贺玉山13年,贺彬10年,王宏仁10年,贺占胜7年,陈培峰6年,朱绪平5年,白光军3年(曾因抢劫、盗窃被判8年,合并执行8年半),孙世慧1年。
11.2007年10月,陕西省高院再次发回重审。
12.2008年11月,榆林市中院第四次一审判决。判处朱继锋无期,贺玉山13年,白光军8年(合并执行12年),陈培峰6年,朱绪平3年6个月,孙世慧1年。对王宏仁、贺占胜一审宣告无罪。
13.2009年9月,陕西省高院第四次发回重审。
14.2010年8月11日,经榆林市中院和榆林市检察院“联合指定”,由榆阳区法院一审开庭,尚未宣判。
两个家族的命运都改变了
2010年8月16日,党岔镇枣湾村。
65岁的王宏英在窑洞前干活。长达9年的精神折磨,让她看起来脸有些浮肿,眼角时有泪光。
9年前,因为高怀堂酒后闯入家中,吓得她此后卧病数月。当时丈夫、儿子都不在家,儿媳妇知道后,气不过报了案。“没想到,给一家人带来了这么大的难。”她喃喃地说。
因为高怀堂的死,她的丈夫、女婿、儿子、小叔子、娘家的兄弟都被卷进案件,至今还没有等来一个结果。羁押时间最长的女婿,已经在看守所度过9年。“当时,我们全家的男人都被抓光了。案子前后有18个人被抓。所有的亲戚都担惊受怕,随时等着被抓呢。就剩我一个支撑着……”46岁的女儿贺美玲哽咽着说。多年来,她坚信自己的亲人无罪,并一直在为他们奔走呼号。丈夫朱继锋在看守所已羁押9年,她独自支撑着家里开的饭馆,为的是“拯救这个家”。
贺美玲说自己不怨母亲。刚开始家里遭了这么大的难,亲戚们都愤恨,说灾祸都是母亲引起的。“一直过了这么多年,案子还没结果,也相信我们可能是被冤枉的。”
而在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枣湾村,高家和贺家两大姓,也因为这个案件,仇怨日深。
死者高怀堂出事后,留下了年迈的母亲和一对10岁左右的儿女。此后的诉讼中,高的母亲、妻子和儿女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向贺家提出民事赔偿20余万元。但法庭每次判决不过8万多元。他们也一直在上诉。
在丈夫死去几年后,高怀堂的妻子改嫁了,两个孩子,如今一个还在上学,一个在打工。“这个案子,把我们一家人也苦恼坏了。”8月19日,高怀堂的哥哥高怀玉对记者说。
高怀玉也怀念没有出事前的宁静生活。他说,曾经,他们两家关系很好,到现在贺玉山还欠着他5000元呢……后来因为弟弟高怀伟竞选村长,贺玉山落选,两家人有了些矛盾。到后来,高怀堂闯了贺家,他还曾去贺家调解过。如果调解成,也就不会出这么大的事了。
“我坚信弟弟就是他们一家人打死的。我弟弟和别人又没啥仇怨。不过当时公安机关事情太多,有些证据可能没有做扎实而已。”高怀玉说。
多年来,一直在外包工的高怀玉坚信案件没错。他认为公安机关办这个案子“把力出扎了”。对贺家人称遭到刑讯逼供的说法,他的看法是:“不上刑,人能承认自己杀人吗?不翻供,那要死人呢,所以,他们翻供也正常。”
被告人称遭“刑讯逼供”
在长达9年、悬而未决的朱继锋团伙杀人案中,被告人翻供、证人“反水”的现象几乎贯穿始终。
从最初的5名被告,到后来的9名被告,几乎都在公安机关做了有罪供述。事实上,9名被告中,只有贺玉山和陈培峰 (朱继锋表弟)两人,始终没有供认犯罪。陈在2007年6月11日已羁押满6年,被“刑满释放”,如今仍在上访,“讨要清白”。
第一次开庭时,朱继锋曾当庭出示一件血衣,向法官陈述说是被刑讯殴打的证据。而王宏仁也曾在3次开庭中向法官出示自己掉落的牙齿。
2010年8月,王宏仁、贺占胜以及另外4名被告人,分别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们都称自己在侦查阶段受到了逼供,都说曾遭遇“大雁南飞”、“二郎担山”等“刑讯姿势”的折磨,其中的细节描述基本相同。
6名被告人都称自己曾被殴打得无法忍受,试图自杀过。王宏仁说自己曾试图以头碰撞铁柜,贺占胜则说自己曾在上厕所时,试图滚下楼梯。
但所有这些关于刑讯逼供的指控,并未被法院认定。榆林中院在第三次一审判决中称:“(被告人)辩称侦查人员在侦查期间对其刑讯逼供之理由,无证据证实,不能成立”。
榆林中院的罗岚检察官,在2005年前一直任此案的公诉人,她表示,被告人虽多次称遭受刑讯逼供,但检察院几经调查,包括找到同监室的人来证明,查看了他们进看守所时的身体检查笔录等,并未发现相关证据。
证人“反水”
另外,除了被告人翻供,此案中,关键证人孙长国的“反水”,也给案件平添“尴尬”。
孙长国在2001年4月24日被办案人员带走询问,并在4月25日和26日做出3份笔录。笔录中,孙称自己当天买药回来,看见朱继锋等人打高怀堂。
但孙随后就向检察院控告,称自己被公安局带去57个小时,连夜逼问,曾被用“铐子铐”、“抽耳光”,只好捏造了目击现场的情节。并称自己当天帮别人修完拖拉机后,一直和朋友在家喝酒。在2001年6月,孙还曾给被告人家属贺美玲写过一份自己“被逼迫”的证明。
孙长国自己推翻的笔录证言,在第一次一审判决中,未被采用。法庭认为:“此证言与各被告人供述吻合的情节有矛盾,孙长国后一直推翻该证言,故对其在侦查阶段的证言不予采信。”但是,这个证言在后来的3次一审判决中又被采用了。其中,榆林中院的第二次一审判决中认为:“虽然该孙后来又证明上述证明系公安人员刑讯逼供所取得,但同时承认后来的证明是被告人家属多次找他作的,故对其在公安机关作的证明予以认定。”
办案人员:被告当年有串供 案子没问题
对被告人指控曾遭受刑讯逼供,当年的办案人员并不吃惊。
“被告人翻供很常见。”榆阳区公安局民警张某说。他认为这个案子没问题。“唯一的遗憾是我们破案时,距离案发时间长了,证据很难收集。不过我们后期做了大量工作。”他说。
一个说法是,此案件发生后3个多月,发生了震惊一时的横山县马坊爆炸案。当时榆林地区的警力大量抽调去办这个案子,警力不足,导致了此案中一些证据未收集到位。
张某还记得这个案子有“串供”。从判决书中可以看出:在朱继锋被关押在佳县看守所时,朱妻曾捎去衣服,里边夹有纸条和布条,内容包括“3月24日白天你和某某等扎金花……下午一直在做饭,7点来了某某……”等内容。不过纸条和布条后来被截获,并未到达朱的手中。
辩护律师吴文也记得这个情况。他说,虽然串供最终没有完成,但因为当事人家属的错误行为,使得案子更加复杂,也使得公安机关坚信朱继锋等人有罪。
记者试图联系当年的另外几名办案人员,但他们大部分都已升至更重要的岗位,都对记者称自己不清楚此案。
当年的检察官罗岚也认为此案并没有什么问题。8月20日,她告诉记者,后来因为被告人要求回避,她就没有再接手这个案子。
“当时案件曾退回补充侦查两次,在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期间,公安机关发现了新证据,所以我们撤回了起诉。后证据补充回来后,又重新起诉。”她回忆说,案子在法院那边拖的时间比较长,但在检察机关、公安局这边没有超出期限。
对证人孙长国的“反水”,罗岚说,这个人在推翻自己的证言后,公安机关找他做笔录,他说了句:“两边都是乡亲,我为了腾利身子。”这句话让她印象深刻。
至于案件证据是否存在问题,罗岚表示,这都是检委会定的案子。意指案子最终起诉也是经集体讨论决定的。
“案子侦查结束后起诉到法院,其实和我们公安机关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法院如果认为他们不构成犯罪,可以直接判决,现在拖了这么长时间,估计是法院也不能确定吧。”8月21日,榆阳区公安局政工科一位负责人说。(江雪 崔永利)
历经9年,这起至少改变10个家庭(9名被告、1位被害人)、两个家族命运的“团伙杀人案”仍未查清真相,其间流逝的不仅是人的自由,也有程序正义应有之尊严。
“朱继锋是我们看守所关押时间最长的嫌疑人了。”2010年8月,榆阳区看守所一位民警说。
从2007年1月开始,“朱继锋团伙杀人案”中,陆续已有6名被告人走出看守所。他们或是已服满一审判决确认的刑期,如贺彬、陈培峰等,或是被一审确认无罪,如王宏仁、贺占胜。
作为“主犯”的朱继锋从2001年4月28日被刑事拘留,此后历经检察院起诉,榆林中院4次一审,陕西省高院4次发还重审,案件尚未终审判决。迄今为止,朱已在看守所度过了从37岁到46岁的9年时光。
2010年8月11日,一直由榆林市中院审理的该案,在榆阳区法院启动第五次一审程序。公诉方也从榆林市检察院改变为榆阳区检察院。“案子其实是降格处理了。”8月20日,榆林市检察院公诉处一位检察官说。
超期羁押引起最高检关注
“如果按照最近一次开庭算的话,羁押期限又快到期了。我们下个月就要发案件指示函,提醒法院案件即将超期。”8月20日,榆阳区检察院监所科副科长刘殿亮说。
监所科负责监督看守所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情况。朱继锋作为犯罪嫌疑人,羁押长达9年,这在刘殿亮的印象中是比较罕见的。
不过,他纠正了“超期羁押9年”的说法,解释说:“案件其实一直在间断性地延期。”
刘介绍说,根据法律规定,刑事案件从起诉时算起,其时限应该是两个月再加45天。案子起诉到法院,期限一个月,审判再一个月,案情复杂的,延长45天。那么,朱继锋案这次启动第五次一审程序,从5月20日榆阳区检察院起诉算起,应该是在9月5日到期。
纵观朱继锋案子,从每一次起诉,到法院二审发回,平均下来,这个程序大约要一年多时间。“案子在区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都没有超期。主要是省高院和中院对案子认识不一致,多次发回重审,所以一直到今天还没结案。”刘殿亮说。
在不久前的全国清理超期羁押行动中,榆阳区检察院向上级汇报了这个案子。从2010年7月开始,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关注此案。如今每隔半个月,榆阳区检察院监所科就要向上汇报一次朱继锋案的进展。
“犯罪嫌疑人长期羁押在看守所,不仅使当事人一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未经审判,却长期失去人身自由,也给监所管理、司法资源等带来麻烦,所以,超期羁押一直是刑事诉讼的一个痼疾。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一直在下大力气,在各地清理超期羁押。”说到此案,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学专家告诉记者。
在此案中,至今关押着的被告还有贺玉山。贺是朱的岳父。贺玉山从2005年12月被刑拘,至今羁押也已5年。另一名被告白光军,因有另案在身,如今在内蒙古服刑。
区法院审杀人案 管辖引争议
2009年12月,9名被告人分别接到榆林中院的开庭通知,称将在12月16日再次一审开庭。这是省高院第四次发回重审后,再次启动一审程序。但几天后,这一通知被撤销。榆林市中院和榆林市检察院“联合指定”案件交由榆阳区法院审理。
2010年8月11日的庭审中,一开庭,律师就向法庭提出了管辖权异议。
辩护律师段平生提出,根据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在刑诉法第20条中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一审刑事案件。
“这起团伙杀人案,一直由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这次却交由区检察院公诉,区法院审理,这不符合法律关于杀人案件管辖权的规定。”段平生说。这位老律师曾在全国内务司法委员会工作,参与过刑诉法的修改等调研工作。
段平生律师搬出一个规定,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6部委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5条规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删除了原来关于“上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交由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的内容。根据这一修改,对于第一审刑事案件,依法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不能再指定下级人民法院管辖。
“立法的本意,是保证刑期比较高的案件能到高一级的法院审理。这个规定,也是对可能剥夺终身自由甚至生命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法律审判的管辖要更慎重,以体现对生命权和人的终身自由权的敬畏。”段平生认为。
西北政法大学一位刑诉法专家告诉记者,像这样指定到区法院审理,对被告人来说,将来上诉,就只能到中院。而中院过去曾4次做过对被告人不利的一审判决,并被高院发回重审。那被告人肯定不愿意。“这样,有可能把被告人得到二审救济的机会丧失了。”他说。
但他也指出,案件交由榆林,就意味着案子可以“消化”在榆林。有知情者介绍,案子下放到区法院,而区法院的判刑不超过15年。这意味着案件降级,也意味着被告人可能得到较轻的刑罚。“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子,原则上要宣布无罪。但现实中,各地往往会选择做一个留有余地的判决。这如今是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即在有外部压力,既不允许判重刑,也不允许判无罪的情况下,法院作出这样一个选择。”北京大学刑诉法学专家陈瑞华教授谈到佘祥林等案时说。
事实上,震惊一时的佘祥林案件也曾被下放到区法院审理。
在8月11日的庭审现场,榆阳区政法委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中院指定区法院审理,我们也没办法。”
疑罪从无,说来容易做来难
从2002年作出第一次一审判决,到2008年11月作出第四次一审判决,虽然省高院每次发回重审的理由都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榆林中院始终“不改初衷”,认为案件证据之间互相可以印证。
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依照法律规定,案件每次发回重审,都要另外组成合议庭,而一个合议庭至少要3个人。这个案件几上几下,以致后来在榆林中院“都找不到法官组成合议庭了”。
“判决书并不是法官的个人意志,都是由审委会决定的。”知情者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朱继锋团伙杀人案”在2001年案发。当时,榆林中院院长丁成年刚刚到任。丁院长2009年底才卸任离开榆林中院。记者多次致电丁院长,希望了解朱继锋一案的相关情况,但他一直未予回应。
2007年,在第三次一审判决作出后,被告人又上诉到省高院,这次,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宣炳昭、王政勋等3位学者代理了此案。
依照当时的惯例,刑事案件二审都是书面审理,很少直接开庭。但因为此案案情复杂,陕西省高院刑庭的法官还专程到榆林,在本地开庭审理此案。
“那次法庭效果很好。律师辩护很到位,还有多名证人出庭作证。”一位辩护律师这样告诉记者。
但当被告人和辩护人都以为法庭会直接改判时,案子却发回到榆林中院,开始了第四次审判。
在2004年省高院第二次发回重审的裁定书中,审判长是雷建新法官。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的雷建新,刑事审判经验丰富。在这份裁定中,合议庭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
2009年12月,雷建新从省高院刑一庭庭长调任榆林中院。2010年7月,被任命为榆林中院院长。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精神,如果证据不足,无论有多大的嫌疑,也得疑罪从无。不过疑罪从无这4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旦法院认定无罪,那就意味着这是错案。无论是检察院还是公安机关,都有错案追究制度。接下来的问题太多了。”一位榆林当地的资深司法人士告诉记者。
这位人士认为,如果省高院改判,榆林中院的压力就会少很多。但他也说,因为法律对此并没有明确规定,这种情况高院很少直接改判,大多都会发回重审。
“这是近年来司法环境并无好转的一个表现。”省高院另一位资深法官告诉记者。过去高院每年还会宣布几个无罪的案件,近两年来,越来越少。法官被要求“顾大局”,不能只依据法律的规定办事。
“有罪或无罪,这其实是一个理念的碰撞。”这位熟悉此案的法官说。“刑法的本意不仅是追诉犯罪,也要保护人权。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就应该疑罪从无。但在中国,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他认为,从这点上来看,本案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刑事司法的标本。